非洲语言文化研究 | “新非洲流散” :奇玛曼达·阿迪契小说中的身份叙事 (文/袁俊卿)


主 编:李洪峰
“新非洲流散” :奇玛曼达·阿迪契小说中的身份叙事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袁俊卿
摘要: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阿迪契在长篇小说《紫木槿》《半轮黄日》和《美国佬》中,有意无意地勾勒出非洲流散者身份认同的嬗变过程:从本土流散者的不知道“我是谁”或“我应该是谁”,到为了追寻自我的民族身份认同而试图构建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比亚夫拉共和国”,再到重新认同“尼日利亚”这个多民族国家。一国之内,某个民族常以其他民族为参照,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由于冲破了时空阻隔,个体或群体面临的不再是本国内的其他民族,而是全球化权力格局中的其他国家,尤其是英美等西方大国。况且,个体、民族和国家的身份构建不仅需要自我认同,还需要“他者”的认可。身份问题关乎民族、国家的兴亡,同时,它也是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设置的一个“陷阱”,即发展中国家的个体要想得到发达国家的“承认”,就必须尽量摆脱母国的“痕迹”,逐渐“他者化”,而“他者化”的过程就是自身主体性被他者塑造的过程。
关键词:“新非洲流散”;主体性;奇玛曼达·阿迪契
2021年,坦桑尼亚裔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毫不妥协并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并关切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的精神(袁俊卿,2021:56)。“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其实就是非洲流散者的命运。古尔纳的获奖,让非洲流散(African Diaspora)以及与之相关的“流散性”主题再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实际上,“‘黑人流散’或‘非洲流散’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或60年代才被广泛使用”(Cohen, 2008: 39)。流散研究专家乔治·谢泼森(George Shepperson)和约瑟夫·E·哈里斯(Joseph E. Harris)认为,流散被用来描述非洲人的经历,“是在1965年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举行的非洲历史国际会议上使用的,也可能是在那次会议上创造的”(Patrick,2009:3)。可以说,“‘非洲流散’一词的现代用法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学术和政治运动的产物”(Zeleza&Eyoh,2003:6)。此时该术语主要用来描述因奴隶贸易和受殖民主义影响而被迫流离海外的非洲人。对他们来说,家园是一个神秘的、理想化的地方,难以抵达,无法回返。到了20世纪80年代,尼日利亚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新非洲流散”(New African Diaspora)的现象,此阶段的流散者大都是相对自愿地移居海外。他们更加自由,与故国保持着密切、稳定的联系,且拥有返回故园的可能性。奇玛曼达·阿迪契(Chimamanda Adichie)、塞菲·阿塔(Sefi Atta)、赫隆·哈比拉(Helon Habila)、克里斯·阿巴尼(Chris Abani)、海伦·奥耶耶米(Helen Oyeyemi)和泰耶·塞拉西(Taiye Selasi)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在21世纪前20年出版了许多代表性作品,形成一股不容小觑的文学力量,这也是尼日利亚英语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特点。
众所周知,身份问题是流散研究的核心问题,非洲流散也不例外。从整体来看,新非洲流散者的身份问题经过了三重嬗变,这三重嬗变在尼日利亚第三代代表性作家奇玛曼达·阿迪契的创作历程中得到了典型且隐秘地展现。在其长篇小说《紫木槿》(Purple Hibiscus,2003)、《半轮黄日》(Half of a Yellow Sun,2006)和《美国佬》(Americanah,2013)中,阿迪契勾勒出了新非洲流散者身份认同的嬗变过程。(1)对于本土流散者来说,欧洲殖民者的强势入侵和殖民统治瓦解了他们的主体性,令他们的身份迷失了,不知道“我是谁”。这种迷失与异邦流散者的身份迷失具有同构性。(2)在国家独立之初,尤其是在多民族国家中,在其他民族的对照下,本土流散者自身的民族身份得以凸显,并且为了寻求自己的身份,他们甚至试图建构一个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种族矛盾则加剧了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意愿。但是,这种国家之内的个别民族追寻自我身份的行为严重挑战了业已存在的现代国家的主权,极易爆发冲突与战争。(3)异邦流散者由于跨越了国界,来到异国他乡,参照标准不再是自己祖国内的其他民族,而是全球体系中某个具体的目标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在西方国家与非洲这个维度中,异邦流散者不再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是国家身份,移居国也更倾向于确认流散者的国籍归属。参照标准的变化带来了身份认同的变化,或者说,参照标准的改变促进了身份认同的转变。其实,对于非洲流散者来说,无论是否发生跨越国界的行为,他们都或隐或显地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因为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已经把他们的语言、教育体制、政治模式、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深深地嵌入到非洲社会的肌体之中,生于斯长于斯的非洲人不仅受到本土习俗的影响,也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染。阿迪契对于身份问题的探讨,就是试图在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张力下重获自我身份认同,重建完整的主体性的一种尝试,是争取并掌握话语权,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摆脱殖民和后殖民话语的重要步骤。因为“帝国主义的描述从来就不是一种中立的客观表述模式,而是一种高度主观的欧洲中心主义话语,在道义上有利于殖民者”(Rushton,2014:184)。只有发出自己的声音,与西方话语进行抵抗、博弈和对话,才能消解业已存在的西方国家对非洲刻板、僵化且单一的负面印象。
1 本土流散者的身份迷失:“我是谁?”
欧洲殖民者抵达非洲①以前,非洲大陆有着自己的传统习俗和族群归属。“迟至1880年,非洲大陆约有80%是由自己的国王、女王、氏族和家族的首领以大小不等、类型各异的帝国、王国、村社共同体和政治实体的方式进行统治”(博亨,1991:1)。但是,欧洲的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逐渐改变了这种状态。加纳历史学家阿杜·博亨(Adu Boahen)指出,1880年到1900年是欧洲殖民者对非洲的征服阶段,1900年到1919年是殖民占领时期。罗伯茨(Roberts)则认为,到了1905年,非洲大部分地区已经被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瓜分,非洲人几乎完全沦为异族统治的对象。从人口规模和土地面积来看,英国无疑是统治非洲的最为重要的帝国力量(罗伯茨,2019)。“到了1914年,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是仅有的例外,整个非洲大陆全都沦为欧洲列强统治下大小不等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通常在自然条件上远比原先存在的政治实体大得多,但往往同它们甚少关系或竟毫无关系”(博亨,1991:1)。殖民列强不顾非洲人民的反对,私自划分势力范围,打破了非洲传统的地理、文化边界。而且,外来宗教、商店、行政机构和教会学校等一系列的殖民机构对非洲本土传统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对非洲来说,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推翻了整个古代的各种信仰和思想,以及古老的生活方式。它使整个民族面临突然的变化。举国上下,毫无准备地发现自己被迫要不就去适应要不就走向灭亡”(博亨,1991:1)。有着“非洲现代文学之父”之称的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在《瓦解》(Things Fall Apart,1958)中就描绘了伊博族的传统文化遭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破坏的过程,主人公奥贡卡沃也在本土习俗和外来文化的双重夹击之下上吊而亡。这种状况具有普遍性。“若干世纪以来的生活准则遭到破坏的过程,不仅扩展到曾经沦为殖民地的国家,甚至扩展到曾经保持住国家独立的埃塞俄比亚”(尼基福罗娃,1981: 1-2)。非洲的传统文化遭到瓦解,非洲人的精神世界遭到震荡和颠覆。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在《大河两岸》(The River Between, 1965)中这样写道:
白人的到来给人带来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难以言喻的东西,这种东西朝着整个山区长驱直入,现在已进入心脏地带,不断地扩大着它的影响。这种影响造成了山里人的分裂,而穆索妮的死就是这种影响的恶果……自从她死以后,时局的发展使人感到担忧,表面上人们保持沉默,但实际上在多数人的心里,虔诚和背叛两种意识却在剧烈地相互斗争。(提安哥,2015: 92)
对于非洲原住民来说,到底是忠于部族传统,做一名传统主义者,还是背弃传统,做一名基督徒?他们拿捏不定,犹疑不决。故而,虔诚和背叛这两种意识在其内心深处剧烈地相互斗争。《大河两岸》的主人公瓦伊亚吉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传统主义者,而是“中间派”。这种貌似“公允”的立场和态度实则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双重塑造的结果,而这两种文化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在瓦伊亚吉的脑海中占据主流。也就是说,在外来文化和宗教的冲击与塑造下,非洲原住民的身份迷失了,不知道“我是谁”或“我应该是谁”,他们处在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加纳作家阿玛·阿塔·艾杜(Ama Ata Aidoo)在《幽灵的困境》(The Dilemma of a Ghost,1965)中塑造的阿托·亚乌森亦是如此。他梦到一个幽灵,上上下下徘徊,对他唱着歌:“我应该去海岸角,还是埃尔米纳?我不知道,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我不明白”(艾杜,2017: 41)。这种徘徊、摇摆的状态表明,他们的主体性身份认同还没有建立起来,从而变成了典型的本土流散者。
由于殖民者推广殖民语言、传播基督教、侵吞土地、实行种族隔离和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非洲原住民在自己的国土上被迫进入一种“流散”的文化语境中。他们失去了家园,在自己的土地上流亡;他们被迫接受宗主国的语言,甚至禁止使用本土语言,但是他们又无法完全抛掉部族语言;他们在自我身份认同方面产生了纠结与疑惑,在到底是做一名传统主义者还是基督教徒之间游移不定;他们的灵魂受到西方价值观的统摄,而又难以与传统文化完全剥离,从而在心灵上造成一种既不属于“此”也不属于“彼”的中间状态。(朱振武、袁俊卿,2019:144)
所谓“本土流散”,是因为非洲原住民虽然没有跨国界的生存经历,但显然,本土流散是对非洲人的精神样貌和心理状态的一种概括性描述。在非洲英语文学中,本土流散具有普遍性,如恩古吉·提安哥的小说《孩子,你别哭》(Weep Not, Child,1964)中的恩约罗格、《暗中相会》(A Meeting in the Dark,1974)中的约翰、伊各尼·巴雷特(Igoni Barrett)的小说《黑腚》(Blackass,2015)中的弗洛、库切《夏日》(Summertime,2009)中的马丁与约翰·库切,等等。在《大河两岸》中,恩古吉对非洲原住民在异质文化张力下的精神状态描写得比较直接,主人公的心路历程直接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但在奇玛曼达·阿迪契的第一部小说《紫木槿》中,康比丽的父亲尤金就是一位典型的本土流散者。只不过,尤金的内心冲突和心理波动较为隐秘,需要读者条分缕析,层层剥离,才能窥见其心灵深处的“惊涛骇浪”,体悟到他内心的撕裂之苦,领略到那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震颤。
前布克奖评委杰森·考利(Jason Cowley)认为,《紫木槿》是其读过的继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的《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 1997)之后最好的处女作(Anya,2005)。这部作品主要描述了康比丽“在前往阿巴和恩苏卡的旅途中,通过与祖父努库、姑妈伊菲欧玛及其家人的接触,逐渐改变了性格”(Ojaide, 2012: 34)并逐渐成长的故事。康比丽的父亲尤金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妻子、儿女的一切日常生活都必须坚守天主教信条,否则就是犯了大忌,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康比丽和扎扎因为私藏已去世的爷爷的画像,而遭到尤金的暴力相待。尤金认为魔鬼已经来到了家里,而他不允许魔鬼的出现。他用力踢着康比丽,“他越踢越快……他踢啊,踢啊,踢啊……一股咸咸的热乎乎的东西流进我嘴里。我闭上眼睛,滑向了无声之境”(阿迪契,2016: 166-167)。在尤金的暴力踢打下,康比丽内脏出血,断了一根肋骨,差点一命呜呼。但是尤金表面看似冷酷无情、暴力血腥,其内心却异常挣扎。康比丽躺在医院的床上,“爸爸的脸离我很近,我们的鼻尖简直碰在了一起,不过我还是可以看出他目光柔和。他哭着说:‘我心爱的女儿。你不会有事的。我心爱的女儿’”(阿迪契,2016: 167)。康比丽从小就在父亲的规训下接受了天主教信仰,没有选择的余地。“我是天主教徒。这是一种身份,虽然我没有太多的选择,但我已经拥有了它”(Adebanwi, 2004)。当西方传教士一手捧着“上帝之书”,一手握着枪支来到非洲的时候,非洲原住民无论是在宗教信仰还是军事实力方面都是无力抵抗的。从这个层面来讲,尤金强迫康比丽等人信奉天主教的过程就是西方殖民者向非洲传播宗教的隐喻。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寓言。尤金的父亲努库是一位传统主义者,有着本部族的传统信仰。在尤金眼中,他的父亲就是异教徒,充满着邪恶和罪恶。“尤金谴责他父亲对木石之神的空虚崇拜,并相信只有他的皈依才能使他从空虚中得到救赎”(Strehle, 2008: 108)。努库自始至终也没有听从尤金的劝说,没有改信天主教。为此,尤金也断绝了与其父亲的来往。努库死后,尤金原本希望按照天主教的仪式举行葬礼,但遭到伊菲欧玛的强烈反对,无奈之下,尤金还是以传统的方式埋葬了父亲。“我给伊菲欧玛送了钱办葬礼,我给了她所需要的一切……为了我们父亲的葬礼”(阿迪契,2016:156)。尤金的妻子比阿特丽斯也时常遭到暴力,只因为她无法生出更多的儿子。尤金必须恪守天主教对婚姻中一夫一妻制的规定,但是又无法摆脱伊博族中富裕人家应该多妻多子的传统习俗。这种家庭暴力在尼日利亚青年作家欧因坎·布雷思韦特(Oyinkan Braithwaite)的首部长篇小说《我的妹妹是连环杀手(My Sister, the Serial Killer,2018)中也有着重体现。阿尤拉未成年时便时常遭受父亲的暴力,长大之后,她对男性表现出一种既需要又恐惧的两难情感。
康比丽、扎扎和比阿特丽斯等人的遭遇表明,“精神的非殖民化只能发生在非殖民化的家庭中——这成为尼日利亚走向独立的必要的第一步”(Strehle, 2008:107)。如果一个家庭也处在殖民化的境地之中,那么,何谈精神的独立自主?很大程度上,家庭就是国家的象征。“尤金之所以如此,正因为受到西方文化和非洲文化这两种并非势均力敌的异质文化的双重塑造,从而处在一种分裂、纠葛的状态中”(朱振武,2019: 57)。《紫木槿》的叙述者是康比丽,而不是尤金,所以尤金的内心世界是隐而不彰的。如果尤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那么其内心深处的撕扯、断裂之苦和游移徘徊之状定会表现得十分明显。流散是指“个人或群体选择离开母体文化而在异域文化环境中生存,由此而引起的个体精神世界的文化冲突与抉择、文化身份认同与追寻等一系列问题的文化现象”(张平功,2013:88)。这也是“全球移民、大流散时代每个种族群体都无法完全回避的”(杨中举,2019:131)问题。尤金就面临着精神世界的冲突与抉择的问题,他无法彻底做一名天主教信徒,也无法斩断与传统习俗的瓜葛,更不能置家庭伦理于不顾而六亲不认。尤金处在一种深度流散的境况之中,在身份认同的层面,即在到底做一名传统主义者还是天主教信徒之间徘徊不定、纠结游移。①他在精神的暗深处不知道“我”是谁或“我”应该是谁。这就是本土流散者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但是,本土流散者的身份认同并不是永远迷失的,他们终将迈出探索自我身份认同的步伐。阿迪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半轮黄日》就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
2 建构新的民族国家身份:成为“比亚夫拉人”
在《半轮黄日》中,奥兰纳和奥登尼博对身份问题的讨论,以及伊博族对国民身份的争夺和抗争,就是本土流散者获取自我身份认同和他人对自我身份认可的一次努力尝试。“由于对共同历史的认识是任何民族想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半轮黄日》是一部历史小说,这是阿迪契的小说构成民族认同文本的最明显方式”(Feldner,2019:40)。奥登尼博是恩苏卡大学的一位讲师,时常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某些国内外的重大议题,如去殖民化、泛非主义和民族独立等问题进行探讨。其中,“身份”问题就是重点议题之一。奥登尼博坚持认为非洲人的唯一身份就是部落。
“我认为非洲人唯一的真实身份是部落……我之所以是尼日利亚人,是因为白人创立了尼日利亚,给了我这个身份。我之所以是黑人,是因为白人把‘黑人’建构得尽可能与‘白人’不同。但在白人到来之前,我是伊博族人。”(阿迪契,2017:22)
奥登尼博认为,“尼日利亚人”这个身份是白人给予的。实际上,“尼日利亚”这个现代国家确实是白人建立的。“1914年,英国总督合并了北部和南部的保护区,他的妻子挑了一个名字,由此诞生了尼日利亚”(阿迪契,2017:128)。而且,奥登尼博之所以是“黑人”,也是白人建构出来的。白人到来之前,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黑人”。自我身份需要“他者”的对照才能凸显出来。在一个全是同样肤色的群体中,群体成员并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肤色有什么与众不同。在《美国佬》中,伊菲麦露从美国回到尼日利亚,深切的感受即是“我感觉在拉各斯下了飞机后,我不再是黑人了”(阿迪契,2017:482)。回到祖国,那种在美国才会凸显的种族身份便消失了。奥登尼博认为自己的首要身份便是伊博族人,但是埃泽卡教授与其意见相左。埃泽卡认为,奥登尼博之所以意识到自己是伊博族人,也与白人息息相关。“泛伊博族的理念是面对白人的宰制才产生的。你必须认识到,今天的部落概念也与民族、种族等概念一样,是殖民的产物”(阿迪契,2017:22)。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奥兰纳与奥登尼博持相同立场,他们是“革命恋人”。奥兰纳曾经多次参加伊博族联盟在姆巴埃齐舅舅家举行的集会。在这种政治聚会中,伊博族男人和女人控诉北部地区的学校不接纳伊博族的孩子。所以,他们想筹建伊博族自己的学校。“我的同胞们!我们将盖起我们自己的学校!我们将集资盖我们自己的学校”(阿迪契,2017:41)!这里的“我们”就是指“伊博族”。其他族群对伊博族的排挤,加深了伊博族的凝聚力和民族身份认同。
奥登尼博和奥兰纳的伊博族身份认同具有代表性,他们并不认可“尼日利亚”这个由殖民者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虽然在尼日利亚建国的时候,伊博族就是其中的一分子。这有着深刻的历史因由。尼日利亚在20世纪初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二战以后,英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大为削弱,其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日益高涨。为了延缓各殖民地的独立进程,维护其在殖民地的一己私利以及反对共产主义在非洲大陆的扩张,英国当局开始对其在非洲的殖民政策进行一系列的调整与改革。在尼日利亚,英国的政策调整以20世纪40—50年代相继出台的《理查兹宪法》《麦克弗逊宪法》和《李特尔顿宪法》为标志。这三部宪法均确定了在尼日利亚实行“分而治之”的原则。“分而治之”的原则把国土面积为336,669平方英里、拥有250多个部族的大国分为三个区域:北区(主要由以豪萨–富拉尼族为主的“北方人民大会党”控制)、西区(主要由以约鲁巴族为主的“尼日利亚行动派”控制)、东区(主要是由伊博族为主的“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控制)(刘鸿武,2014:122-126)。这三个区域在民族、宗教、语言以及经济状况等方面差异悬殊,而英国政府正是利用这三个区域的差异企图削弱它们的力量以及减小它们团结抗争的可能性。“地区分治主义作为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政策的结果,事实上已经成为尼日利亚政治的基本特征,它对以后尼日利亚统一国家的稳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刘鸿武,2014:124)。如果说争取尼日利亚的独立这一总体目标可以使得北区、西区与东区的三大政治势力联合起来的话,那么在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亚取得独立之后,这三大政治势力间的矛盾与冲突便凸显出来了。毕竟,这三大政党只是分别代表不同区域的利益,并不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而且,传统的尼日利亚部族都有自己的社会运行模式,“各自为政”,并没有统一的国家经济基础、文化基础与国家情感,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心理。尼日利亚的形成“不是社会经济发展、民族一体化进程的结果,它是在还没形成统一的经济生活、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与文化的时候,就因为非殖民地化的完成而组成新的国家了”(刘鸿武,2014:130)。这就产生了很多问题。“昔日属于同一民族,现在被分割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昔日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民族,现在被分割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相互变成外国人”(陆庭恩、彭坤元,1995:581)。因此,民族间的和谐相处变得十分困难。而且,短时期内,各民族的人民很难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由于这些边界是殖民大国任意划定的,没有考虑到已确立的文化或语言领域,因此,在尼日利亚1960 年独立时,潜在的冲突已经显而易见”(Feldner,2019:39)。没有统一的国家认同,各民族间很容易爆发冲突。
20世纪50—60年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民族主义政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仅在1960 年就有喀麦隆、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索马里和尼日利亚等17 个非洲国家取得了独立,这一年也被称为“非洲年”(Birmingham,1995:1)。到了1980年,除了纳米比亚以外,非洲各国已经全部取得了独立。非洲国家独立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国家意识淡薄、政客对种族情绪的操纵、各层面的腐败、公共服务的缺乏、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缺乏信心、阶级对立、城乡矛盾,等等(Michael,1984)。1966年,以尼日利亚政府降低可可的收购价格为导火索,大批不满的农民以及在选举中失败的政党掀起反抗政府的运动,一批有预谋的伊博族军官趁机发动军事政变,联邦总理与财政部长等高官被杀。伊龙西将军担任尼日利亚国家元首,取消联邦制,建立中央集权政府。随后,政变与反政变频仍,民族矛盾日益激烈。1966年5月,伊龙西政权颁布的“第34号政府法令”严重触犯了北方的保守势力,生活在北方地区的伊博族人遭到驱逐与屠杀,最后发展成大规模的军事暴动,伊龙西被杀。与此同时,东区的伊博族人开始对当地的豪萨–富拉尼族人进行还击。1966年7月29日,北部豪萨族军官发动政变并很快控制了局势,选举戈翁担任国家元首,随即大肆杀害伊博族军官。
(未完)

本文发表于《非洲语言文化研究》第三辑,
更多文章信息可选择下列两种方式:
1、请扫描上方二维码或复制链接(https://sourl.cn/WS3hUn)到浏览器,移步知网下载。
2、关注“北外学术期刊”公众号,后台回复“非洲语言文化研究03”即可获取文章。
期
刊
在线阅读及其下载
在学术期刊官网,查看本刊
https://www.bfsujournals.com/c/2019-07-18/486522.shtml
在知网,查看本刊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DYXX/detai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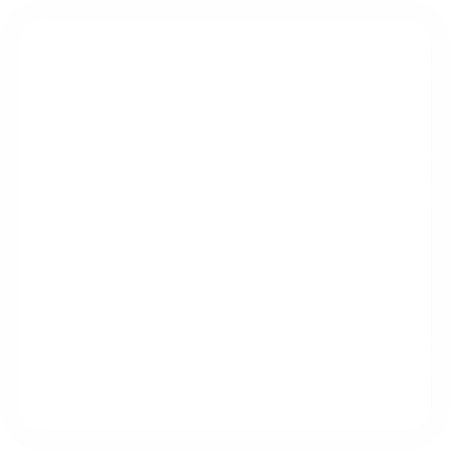
期刊介绍
本刊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主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性刊物,主要发表非洲语言、文学和社会文化等研究领域的优秀学术成果。主要栏目包括非洲语言与文学、非洲社会与文化、中非文化比较与交流、专题研究、学术动态和书评等。
荣誉及数据库收录: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数据库收录,为“2022年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集刊AMI综合评价”入库集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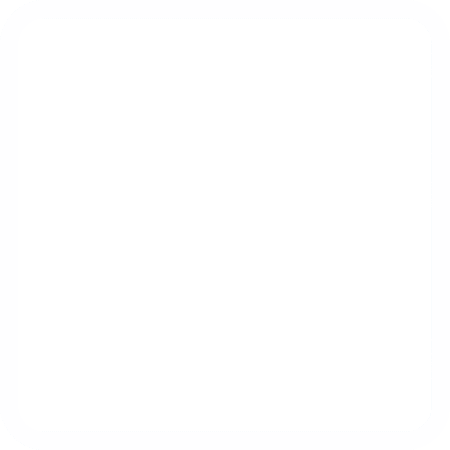
期刊订阅方式
淘宝、天猫电商销售:
单期购买。通过外研社天猫旗舰店购买当期以及过刊。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abbucket=1&id=732578060683&rn=b73c413eac03d7393bf3700278cea3fa&spm=a1z10.3-b-s.w4011-22665586135.34.5bdb37e9DJ6LJr&skuId=5074191241766
往期精选
点击“阅读原文”,获取购买链接
转载请注明来自微信订阅号:北外学术期刊
北外学术期刊官网:https://www.bfsujournals.com/
欢迎分享与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