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研究论丛| 以“脱欧”事件为窗透视英国社会身份认同问题 (文| 韩青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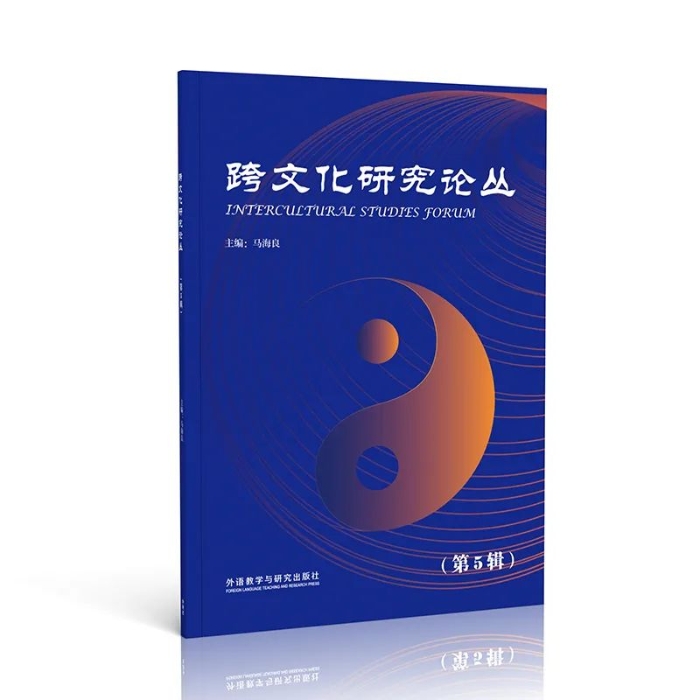
顾 问:胡文仲 Michael Byram
名誉主编:孙有中
主 编:马海良
常务副主编:刘立华
以“脱欧”事件为窗透视英国社会身份认同问题
韩青玉
摘要:英国最大独立社会调查机构NatCen Social Research有关“脱欧”的调查表明,传统左右翼党派政治已无法解释“脱欧”过程中的民意分裂现象,而身份政治在“脱欧”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研究把英国“脱欧”事件放在历史的维度中,从国家、民族、种族三个层面,对此次“脱欧”事件与英国社会身份认同问题间的关系及其背后的历史缘由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所谓的“大英帝国”历史记忆与所谓的“二流国家”现实困境导致国家身份认同错位;民族国家历史事实与联合王国内部离心现实导致民族身份认同强化;多元文化主义传统丧失与移民问题现实凸显,导致种族身份认同冲突。以上三个因素是诱发此次“脱欧”事件背后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族群认同
1 引言
社会身份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是英国社会心理学家泰弗尔(Tajfel)及特纳(Turner)等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他们将“社会身份认同”定义为“个人对其所属特定社会群体的认知,以及该群体成员资格对其具有的情感和价值意义”( Abrams & Hogg 1990:2)。社会身份认同由类化、认同和比较三个基本心理行为历程组成。类化指“我们”和“他们”的区分;认同指接受自己归属的社群身份;比较指自己所在社群较之他者所属社群的优越性。通过以上三个历程,人们构建起了自身属于某个群体的社会身份(Hogg&Abrams1988)。社会身份认同是一个上位概念,包括国家身份认同、民族身份认同、种族身份认同、阶层身份认同等下位概念。
英国最大独立社会调查机构NatCen Social Research有关“脱欧”的调查表明,传统左右翼党派政治已无法解释英国“脱欧”过程中的民意分裂现象,而身份政治在英国“脱欧”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Swales 2016)。身份政治的核心是社会身份认同,泰弗尔认为对社会身份认同的追求是群体间冲突和歧视的根源所在,群体归属意识会强烈影响人们的知觉、态度和行为(张莹瑞,佐斌 2006)。在整个英国“脱欧”事件中,无论是引发英国“脱欧”的起因,公投中的抉择,还是围绕英国“脱欧”方式的争执,无不涉及社会身份认同问题。而Yes与No的二选一公投机制,为“我们”与“他们”的身份划界提供了便利的同时也很容易使得英国社会民意撕裂,社会共识难以达成。因此,英国“脱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场关乎社会身份认同的危机事件。对于英国人而言,社会身份认同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生事件,而是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广泛存在于英国社会的多个层面。然而,这种长期广泛存在的社会身份认同问题在此次英国“脱欧”事件中得到了集中暴发。英国“脱欧”事件无疑为我们深度理解英国社会身份认同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将英国“脱欧”事件放在历史的维度中,从国家、民族、种族三个层面来具体讨论“脱欧”事件与英国社会身份认同问题间的辩证关系及其背后的运作机制。
2 英国国家身份认同错位
2016年,英国最终以全民公投形式,选择了“脱欧”,结束了欧盟成员国身份。回顾英国加入欧盟(前身为“欧共体”)的历史,英欧在大多数日子里彼此缺乏信任与默契,在诸多方面难以达成共识,这导致英国成了欧盟成员国中欧洲一体化进程最低的国家。在一项关于“你是否认为自己既是英国人,也是欧洲人”的调查中,英国一直处于对欧洲身份认同感最低的成员国之列。以2006年为例,66%的英国人认为欧盟身份对英国不利(Eurobarometer 2006)。英国的这种疑欧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和昔日“大英帝国”的辉煌历史有关。这段辉煌的历史不仅为殖民时期的英国构筑了“日不落帝国”的国家身份,也为后殖民时期的“全球英国”身份重建奠定了信心底色。
对外殖民扩张铸就了英国“大英帝国”的辉煌伟业,并使其对欧成功实施了“光荣孤立、大陆均势”的外交战略。这种外向扩张的基因以及这段对欧“均势外交”的历史,致使英国自此不甘委身于欧洲,任由欧洲一体化淹没其大国身份。虽然英国当前国力下降,往日辉煌不存,在世界舞台上彻底沦为“二流国家”,在欧盟内部其影响力也不及德国和法国,但在具有保守传统的英国人脑海中,昔日“日不落帝国”的光荣记忆依然难以磨灭,旧日“光荣孤立”的外交战略仍令其回味,有学者将这种对旧日帝国身份的依恋所导致的身份认同危机称为“后殖民忧郁症”(postcolonial melancholia),并视其为理解“脱欧”事件中英国身份建构和重建的主要途径(Manners 2018)。
在后殖民时代,英国民众对旧日帝国身份的集体怀旧情绪深刻影响了英国在欧洲,乃至在世界的国家身份定位,令其挣扎于“全球英国”的梦想与“二流国家”的现实之间,深陷国家身份错位的危机之中。英国“脱欧”事件在国家层面是英国对其现实国家身份感到不适的一次情绪发泄。正如桂涛(2019:6)所言:“在《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美国最终替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历史写到了一个句点’。但英国人适应这个句点用了100年,他们至今仍在不断调试自己与欧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脱欧’就是最新的一次尝试。”
“全球英国”虽然是“脱欧”后才明确提出的战略构想,但“全球英国”的梦想始终是英国外交努力的方向。二战后,随着原先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地区纷纷独立或回归,虽然英国往昔霸主势力不复存在,但其依然在旧日帝国的辉煌历史记忆作用下,试图在全球主要力量间纵横捭阖,制造影响力,树立有作为的大国形象(王展鹏,夏添2019)。丘吉尔的“三环外交”战略就是对这种梦想追求的充分体现。“三环外交”即英国通过与英联邦、美国和欧洲这三个环节的特殊联系,企图挽救和恢复其在二战中被削弱的国际地位。但是自苏伊士运河事件以后,英国开始意识到其所追求的大英帝国的责任担当与其现实势力和影响力已无法匹配,因而选择回归欧洲,并于1973年加入欧共体。但这一选择只能算是基于经济利益考量后的权宜之计,而非英国心甘情愿之事。自从加入欧盟之后,英国发现自身在欧盟内部处处受到德国、法国的牵制,并未达到预期的主导地位。此种处境显然不符合英国对大国身份的追求,因而在欧盟框架内英国常常表现得格格不入,始终没有签署《申根协定》和同意加入欧元区。“脱欧”似乎成了英国重回世界舞台,重塑英国大国形象、重拾大国地位的必然选择。
2016年,脱离了欧盟羁绊的英国开始重构自身国家身份,明确将“全球英国”定为其“后脱欧”时代的战略愿景。“全球英国”战略不过是丘吉尔“三环外交”战略的翻版,只是优先关系发生了变化,根据“全球英国”战略,发展英美特殊关系是优先选项,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关系次之,英国和主要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居于第三(张飚 2018)。在“后脱欧”时代,英国推出“全球英国”战略旨在通过重建朋友圈重构其世界大国身份。
总之,现如今的英国已非昔日的“日不落帝国”,其影响力已无法与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相提并论,即使在欧盟内部,其影响力也不及德、法两国。但即便如此,因帝国鼎盛期对欧“均势外交”政策而沉淀的“光荣孤立”心理优势使英国社会滋生了一种持久的疑欧情绪,以至于欧洲成了英国人眼中的“他者”。用丘吉尔的话讲,“我们是和欧洲在一起,而不是属于它。我们与它利害与共,但并不被它所吸纳”(陈乐民2014:83)。面对“大英帝国”的历史荣耀与“二流国家”的现实困境,英国人最终选择通过“脱欧”来实现其“全球英国”的未来梦想。这种一味沉迷于历史地位而不顾现实情形变化的错位身份诉求是英国国家身份认同焦虑的表现。
3 各民族身份认同强化
英国是一个多民族王国,由英格兰先后联合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而形成。在联合王国内部,除威尔士与英格兰的联合体相对稳定之外,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与英格兰间的分歧不断。一方面,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不断通过权力下放诉求,在教育、宗教、法律等方面获得了较大自主权,因而也较好保持了各自的民族特性,民族认同得到了不断强化。另一方面,英国在国家治理中未能拿出有效的民族整合手段,导致统一民族身份认同缺失。这两方面因素加在一起,使得苏格兰和北爱尔各自民族身份认同不断得到强化,民族间的共识变得难以达成,民族分裂主义开始抬头。
英国各民族间的裂隙自然也反映在了“脱欧”公投结果中,由于苏格兰与北爱尔兰相对亲欧,大多数选民选择留在欧盟;而威尔士与英格兰,尤其是英格兰中部、东部与东南部大多数民众更为疑欧,大多数选民选择脱离欧盟。最终,“脱欧”派以多数得票胜出。而这一结局与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多数民意相悖,两地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升温,尤其是苏格兰拟采取实质性行动,以全民公投形式决定其是否继续留在英国。
3.1苏格兰民族身份强化再次引发独立诉求
英国“脱欧”公投中,苏格兰62%的选民选择了“留欧”,这让英国“脱欧”是否会导致苏格兰“脱英”再次成为话题。尽管,许多人将导致苏格兰独立诉求的直接原因归结于其自身现实经济利益的考量,诱因是英国政府对其权力下放的制度安排,但深层的原因还是在于统一民族身份认同的缺失。
苏格兰人有着极强的民族认同,他们自视为苏格兰人而非英国人。英国《卫报》发布的一项读者调查显示,只有19%的苏格兰人将英国人身份视为自己的第一身份(Carrell 2011)。自1707年苏格兰被英格兰合并成大不列颠王国一部分后,苏格兰人不断寻求自治空间,始终未将自己视为真正的英国人。通过努力,苏格兰人事实上也争取到了很大自治空间,除了外交、军事、金融、宏观经济政策等事务受到英国政府管辖,在内部立法、行政管理上确实拥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力。尽管如此,苏格兰人还是不甘于被英格兰人统治,于2014年进行过一次独立公投,这次公投虽最终以55%的选民投反对票告终,使其未能脱离联合王国,但其独立之心始终未曾泯灭。2017年,以独立为政治纲领的苏格兰民族党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后,再次提出举行二次独立公投,这次请求虽未得到英国议会批准,但足以表明独立派在苏格兰拥有强大民意市场。
尽管,英国时任首相戈登·布朗在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前出版的《苏格兰与英国应共享未来》一书中写道,“将不同民族拴在一起的东西……是大不列颠殖民帝国崛起的利益与荣耀,是英国的医疗、养老金和最低工资体系带来的统一的社会经济权利,也是两次世界大战中共同作战的经历,是它们将苏格兰与英格兰在过去300年间拴在一起”(桂涛2019:238)。然而,现实的经济、社会利益和共同抵御外敌的作战经历只是苏格兰和英格兰联合在一起之后的共有经历,而在此之前苏格兰作为独立的国家有着更长远的历史。历史记忆和文化差异导致的共同身份认同弱化,很难保证苏格兰不受环境变化影响,而与英格兰保持持续的稳固关系。
苏格兰在很长历史时期里曾与英格兰发生过一系列血腥战争。战争给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伤痕。但与此同时,经过长期独立战争的艰苦磨炼,苏格兰人的民族意识逐渐锻铸成型,民族凝聚力不断加强,独立性不断巩固(Paul 1991)。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这次合并对苏格兰来讲一开始就是基于分享英格兰及受其殖民统治的地区庞大自由贸易的经济利益算计,而对英格兰来讲是基于防止法国以苏格兰为据点打开北方门户的政治利益考量。这种缺乏可靠认同根基的联合极易受经济利益这个变量影响而出现松动现象。从1707年合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200余年中苏格兰受益于英帝国崛起,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苏格兰与英格兰结合得异常紧密,很少有人提出对合并的异议。然而,进入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国势日趋衰落,经济出现萧条,苏格兰再也难以从整个英国发展中获益,这导致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得到了选民和政党的大力支持,其力量由弱到强,地位从政治的边缘上升到政坛的中心,对当代英国国家统一构成了严重威胁(王磊 2011)。1998年,联合王国议会通过《1998年苏格兰法案》,这一法案明令设立苏格兰议会,这使得苏格兰自治能力进一步得到加强的同时也使得其独立诉求进一步加大,最终在冷战后的民族主义浪潮中,苏格兰于2014年举行了独立公投。
而此次英国“脱欧”又一次引发了苏格兰人的独立情绪,要求进行独立公投的音调不断升高。主张独立公投的苏格兰首席部长亚历克斯·萨尔蒙德更是将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宣称为“从属关系”,这无疑是国家认同弱化、民族主义盛行的最好注解。总之,苏格兰民族身份认同的不断增强和统一民族身份认同的缺失导致苏格兰与英国难以同心同向。
3.2北爱尔兰民族身份强化或开启南北统一之窗
由于历史原因,北爱尔兰问题一直令英国非常头疼,对英国领土、主权完整及 政治体制构成了巨大挑战。教派冲突始终是北爱尔兰暴力事件频发的蓄能池。据北爱尔兰议会选举研究(The Northern Ireland assembly election study)的调查,在英国“脱欧”公投中,绝大多数(85%)天主教选民投票选择留欧,而大多数(60%)的新教徒选民选择“脱欧”,在投票留欧选民中绝大多数(88%)为主张南北爱尔兰统一的民族主义者(Garry 2016)。此种情形导致主张南北爱尔兰统一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再度兴起。在爱尔兰政府的推动下,欧盟27国领导人同意,如果未来北爱尔兰地区民众通过公投决定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则统一的爱尔兰将自动成为欧盟的一部分(曲兵 2019)。显然,“脱欧”使得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身份差异得以强化,隔阂再度加剧。
北爱尔兰问题由来已久。1603年,英格兰人征服爱尔兰,从此开始了长达300多年的殖民统治。但军事占领并没有使爱尔兰人屈服,反抗连绵不断。直到1921年底,英爱双方签订《英爱条约》,南部以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本地人为主的26个郡独立,成立爱尔兰自由邦,条约规定爱尔兰自由邦在政治上独立于英国,但仍保留着英联邦成员的地位。而北部以信仰新教的英格兰和苏格兰移民后裔为人口多数的6郡拒绝独立,选择继续留在英国,以地区的身份加入英国。1949年爱尔兰自由邦脱离英联邦成立爱尔兰共和国。与此同时,英国议会通过《爱尔兰法令》,重申如果没有北爱尔兰的直接同意,北爱尔兰将不会终止作为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南北爱尔兰的分裂同时造成了天主教与新教两个教派的冲突,原因在于爱尔兰共和国的居民基本为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本地居民,而北爱尔兰的居民中信仰新教的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移民后裔占绝对多数(2/3),其余是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不同信仰的居民构成是日后北爱尔兰冲突的主要诱因。另外,《贝尔法斯特协议》为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谋求独立留下了机会,根据协议规定内容,只要北爱尔兰通过公投,取得“北爱尔兰的直接同意”,北爱尔兰就可以“终止作为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
“脱欧”后作为英国一部分的北爱尔兰将不再具有欧盟成员资格,而大多数爱尔兰天主教教徒留欧主张强烈,这为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以全民公投的形式脱离英国进而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加入欧盟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
4 种族身份认同冲突
埃塞克斯连续监测调查(essex continuous monitoring surveys,简写ECMS)对英国“脱欧”投票做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研究,结果表明,民众对移民的担忧不仅是造成公投“脱欧”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造成民众长期“疑欧”情绪的主要原因(Clarke et al. 2017)。2016年“脱欧”公投过程中,英国国内反对移民的情绪高涨。在公投中,甚至有民众出于对移民的敌视才去投票,这部份人数远远高于亲移民选民人数(Clarke et al. 2017)。
总体来讲,主张“脱欧”的选民来自经济上处于平均水平之下的地区,这些选民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教长,而且工作不稳定(Goodwin & Heath 2016)。这一群体被认为是被现代化和全球化落下的、抛弃的、遗忘的群体。他们对移民的排斥心理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移民对他们就业、福利的挤占;另一方面是移民参与的恐怖事件攀升。前者因有色移民群体文化程度较低、技术水平不高,导致他们所能胜任的工作与本地底层民众重叠,因而挤占了本地居民的生存空间,由此引发了本地居民与移民之间的族群矛盾;后者是因为多起恐怖事件的参与者被锁定为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极端分子,这导致民众将仇视的矛头扩大到了整个穆斯林群体。民众对移民的排斥进而上升到了种族身份认同层面,据调查,2013年,51%的英国人认为拥有英国血统是真正英国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在英国白人中,这个数字是60%(Park et al. 2014)。另一项调查显示73%的英国白人主张大幅度减少移民,他们认为血统对于真正的英国人来讲很重要(Kaufmann 2017)。
在政策层面,导致种族主义兴起的原因与英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本身的缺陷及实施成效的折扣有关。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原本旨在创造一个柔性同化的大熔炉,但在实践中却因未能树立起共同的价值观,而形成了一种国家认同真空状态(常晶2012)。
历史上,移民曾为英国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二战后,英国出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大量引入移民。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末,大量来自非洲、西印度群岛和印度的英联邦国家的移民进入英国;20世纪70—80年代,亚裔和孟加拉裔移民大量涌入;2004年起,来自捷克、匈牙利、波兰等中东欧新欧盟成员国的移民开始进入。大量外来移民的到来,使得英国成了一个数百个不同族群组成的多元民族国家,民族构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超级多样性特征(Vertovec 2007)。同时,多元民族构成也引发了严重的种族冲突,移民俨然成了“问题一族”,这直接促使英国政府逐步采取多元文化政策,缓和国内族群矛盾、消除种族隔阂,推动国家团结和民族融合。
进入21世纪以来,以美国“9·11”和伦敦“7·7”地铁爆炸为代表的恐怖主义事件频发,加之移民、难民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以及移民与本地居民间的就业、福利之争升级,公众对于多元文化主张的争议自然升温。争议的焦点主要是,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究竟是增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是造成了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多元文化主义在政策层面,由于允许把个人信仰置于公民忠诚之上(Ashcroft & Bevir 2016), 不同族裔文化身份得到保护的同时也使族群认同感得到了加强,不仅出现了因聚集居住而产生的硬性族群隔离现象,而且因教育、就业、生活等方面的区别制度设计,出现了软性的族群隔离现象。这种情形导致移民族群游离于主流社会生活之外,处于自成一体的“平行生活”(parallel lives)状态(Cantle 2001)。尤其是英国境内发生的多起由移民主导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使英国政界高层认识到了民族融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多元文化主义很快失宠,逐渐走向终结。布莱尔在其第二任期内,开始更多提倡英国共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强调融合的责任;布朗上台之后更是直言多元文化主义因过分强调多样性而牺牲了团结;卡梅伦表示,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道藩篱割裂了英国社会(Meer & Modood 2009)。在这种情形下,政治家们试图用一套强调“英国性”(britishness)的公民身份认同价值观取代和整合多元文化主义主张,但这种国家层面的宏观身份认同构建显然无法在短期内奏效。
总之,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失效,加之国家层面的共同价值引领缺位,使得移民容易形成族群抱团心理,并导致“平行社会”现象。尤其在经济下行,财政预算紧缩的情况下,本国人就会把就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不满转嫁到移民身上,导致敌视移民情绪出现,进而引发本国人与移民间的种族冲突。
5 结语
“脱欧”事件至于英国就像一把手术刀,在割裂英国社会的同时,也触发了英国在国家、民族、种族等多个层面历来已久的身份认同危机应激反应。在国家层面,“脱欧”唤醒了昔日“大英帝国”的历史记忆,导致今天已沦为“二流国家”的英国,国家身份认同错位,试图通过摆脱欧盟羁绊,重新走向世界,实现“全球英国”梦想;在民族层面,“脱欧”刺激了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昔日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致使“他们”是英国人,“我们”是苏格兰、爱尔兰人的民族认同进一步强化,留下“谁是英国人”这一统一民族身份认同的悬念;在种族层面,由于英国昔日多元文化主义历史传统丧失,加之国家层面的共同价值引领缺位,“脱欧”致使本国人与移民间的种族身份认同冲突加剧。
英国“脱欧”是当今世界民粹主义、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其所引发的身份认同危机,是全球或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问题之一。英国“脱欧”过程中反映出的国家身份错位、民族整合不力、多元文化主义失效等国家治理能力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帝国意识回潮、民族分裂主义抬头、族群主义兴起等意识形态内倾现象是继特朗普主政美国之后世界范围内所谓“新自由主义”退潮,反全球化右翼保守主义浪潮兴起的又一个例子,值得世界其他国家警醒。
注:本文选自《跨文化研究论丛》第5辑,第106—114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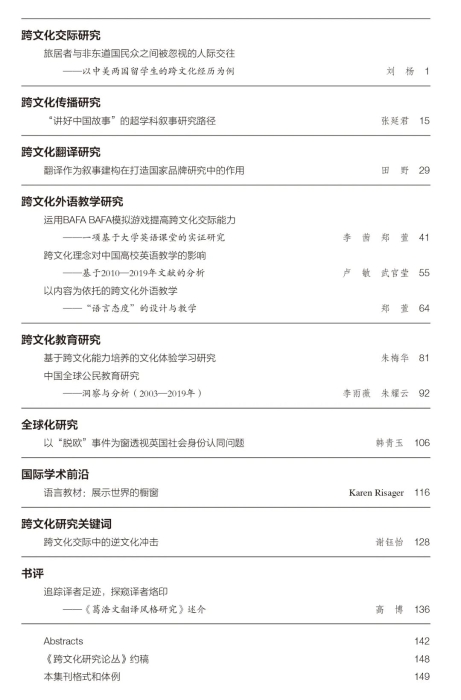
期
刊
在线阅读及其下载
在期刊官网,阅读全文
https://www.bfsujournals.com/c/2019-07-18/486528.shtml
在知网下载期刊全文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KWHL/detail
期
刊
订购信息
天猫旗舰店
单期购买。通过外研社天猫旗舰店购买当期以及过刊。

(请用手机淘宝、天猫app扫描二维码进入)
往期精选
点击“阅读原文”,跳转北外学术期刊官网
转载请注明来自微信订阅号:北外学术期刊
北外学术期刊官网:https://www.bfsujournals.com/
欢迎分享与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