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研究中的语言能力培养与人类学素养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亚非研究》
主编 苏莹莹
提要
区域国别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学科版图中日益受到重视,多学科之间的互动将促进区域国别研究范式的更新。近年来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其在海外社会文化研究实践中所确立的学科规范——掌握对象国的语言并通过与研究对象的密切互动来寻求理解他者的路径,将为区域国别研究中语言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培养提供借鉴。龚浩群从自身参与海外民族志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经验出发,对中国人类学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所可能发挥的作用以及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并就区域国别研究中语言能力培养的内涵问题提出了建议。在她看来,对语言能力的重视应当与培养文化欣赏的能力结合起来,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将从基本的人类学素养当中获得新的理解世界的视角。
关键词:区域国别研究;语言能力;海外民族志;人类学
作者简介:
龚浩群,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泰国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冯健高,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01
一、人类学海外民族志在当代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地位
冯健高(以下简称“冯”):龚教授,作为国内人类学海外民族志领域、特别是泰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方面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您认为人类学海 外民族志在当代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占据怎样的地位?
龚浩群(以下简称“龚”):这个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实然”的情况,就是实际的地位、状况;另一方面是“应然”的情况,也就是说应 该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我想说,从地位角度来讲,“实然”的状况和“应然”的状况之间差距还比较大。我们已经开始做海外民族志,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海外民族志要在区域国别研究当中取得它所应有的地位,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去走,需要几代学人的努力。
我们先谈“应然”也就是理想的状态。如果我们从美国二战以后建立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来看,几乎任何一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里面都会有人类学学者的参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牛可老师写过好几篇关于美国地区研究兴起的文章,里面多次提到人类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如果借鉴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到,实际上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基础性学科,是区域国别研究当中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一。这取决于好几个方面。一方面,海外民族志研 究首先要求人类学学者要掌握对象国的语言,然后通过长期的参与观察来获得第一手资料。这些学科规范的要求使其不同于其他学科如政治学或者经济学,因为它更强调我们要真的走入对象国的社会当中,去看最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如果说国际关系研究以国家和政府间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更多探讨的是舞台上那些比较鲜亮的人物,那么人类学学者则往往研究的是一个社会的主体面貌。我们研究的大多是普通人,不像外交官那样显赫,也不像政治家那样野心勃勃,但正是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即普通人如何把“国家”概念用作“大众想象、理解、评论、批判社会生活的理论工具”(项飙,2010),对我们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发展走向起到很重要的作 用。我们的研究是面向基层社会的,获取的资料也是非常基本的一手资料,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在区域国别研究当中应当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尤其是在经验研究方面的基础性地位。这是从“应然”的状况上来说的。
从中国的实际状况来看,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在 2000年以后才开始发展起来,这是由很多复杂的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一,中国高校的经费在那 个时候开始增长了,出国计划对大家来说也越来越普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海外民族志研究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其二,还有一些非常有远见的个人,像我在北大的导师高丙中教授等,他们在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时代和个人的因素共同促成了海外民族志在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界得到发展。从目前的情形来看,人类学海外民族志能够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基础性的经验研究,但我们目前所做的还远远不够。首先,从地理的覆盖面上来讲,我们的研究还没有覆盖到那么多国家,像非洲,保守估计的话国内做非洲人类学的学者可能不超过十位,但是非洲有那么多国家,人类学的研究区域还没有那么大的覆盖面;还比如中亚的一些国家,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的。其次,从研究深度上来讲,海外民族志研究实际上是需要积累的。你去看美国的人类学研究就会发现,二战以后他们在世界各个区域开展大量的民族志研究,有几代人在积累,比如说导师去做了关于某个区域的研究,然 后学生会接着再做,通过两三代人的持续努力积累一批学术档案资料,在某个问题上有持续长时期的观察和推进,这样才能够取得好的深度。我们的人类学研究在这短短的20年当中还没有完全形成有梯队的研究队伍,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可喜的是,现在的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海外民族志研究的重要性了。我们做海外民族志的人类学学者有更多的机会与不同学科 的学者在一起交流,比如我也会参与国际关系领域的“中泰战略研讨会”,这是华侨大学与泰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合办的年度会议,我很喜欢在这个会上与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一起交流。大家的视角不一样,但恰恰是因为不一样,有时我们对同一个问题会生发出一些有意思的思考,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另外,现在我们人类学的不少博士毕业生也能够到清华、北外、川大、云大、浙师大等高校设立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或者是其他一些以国外研究为主要方向的研究机构(比如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片的各个区域研究所)工作,区域国别研究的大门已经向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者打开了,这也是一个好的兆头。实际上我自己也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现在叫做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工作过5年。我想说的是海外民族志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当中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应该是大势所趋。
冯:您提到不同学科学者的交流,那么,在区域国别研究的框架下,人类学和其他学科之间可以如何互动?
龚:可以请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当中的传统优势学科,比如说国际关系、政治学、历史学或者是国际经济这些学科的学者与海外民族志研究者有更 多的交流、更多的合作和互相借鉴,这个是可以去推动的,也是我们需要去推动的。做国际政治或者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会对时局有很强的敏感性,也就是他们更多地具备从上往下看问题的敏感性,而人类学学者更多是具备从下往上看问题的敏感性,真正优秀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同时具备这两种敏感性。人类学学者如果和区域国别研究当中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有更多的交流合作,将会共同推动区域国别研究取得新进展,这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
另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当中的其他学科也可以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应该有意识地培养基本的人类学素 养。那么,人类学素养指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语言能力。我印象很深的是去开国际泰学研究会议的时候,碰到一些西方国家来的研究泰国政党政治和政府行为的政治学学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会说泰语,这让我比较惊讶。他们的泰语很好,而且他们不仅会说泰语,他们所做研究的问题意识就来自于跟泰国的老百姓交谈之后获得的一手信息,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仅通过看报纸看新闻获得资讯,还通过去街头跟摊贩或者普通市民聊天获取信息,并由此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把握时事的动向,这让我很佩服。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主旨发言人是英国学者,他是做泰国政治研究的,他提出一个问题:怎么去研究泰国的选举制度?他说泰国的选举制度对选举 结果有很大的影响,政府要求选民回到户籍地去投票,但是对于从东北部或者泰国其他地方到曼谷打工的人员来说,他们的户籍地并不在曼谷,这些人回去投票可能得跑好几百公里,成本是非常高的,这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投票率。他从一些很小的角度看到选民的构成以及这些选民的生存境况对他们政治行为的影响,这样的政治学研究就很有意思,能够从细微处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问题。我们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都需要一些人类学的素养,包括学习对象国的语言,去了解对象国普通人的想法,把这些普通人的想法跟我们对于大的形势的判断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可以给出的一些建议。
当然,人类学学者也迫切需要向其他学科学习。人类学学者有时会陶醉于对日常生活中细节的把握,但是我们可能会忽视对于宏观的政治经济 政策和地缘政治的研判。因此,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些跨学科的交流。人类学海外民族志在当代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地位,并不是由我们人类学学者自己说了算,这取决于我们能否做出真正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另外还取决于我们跟区域国别研究的其他学科之间能不能形成积极有效的对话,并共同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范式的革新。
02
二、从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看区域国别研究中语言能力的重要性
冯:刚刚您提到了人类学学者的基本素养问题,提到国外一些国际问题专家的语言能力特别强。那么,您认为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特别是在发 展中国家开展相关研究,学者需要什么样的语言能力?
龚:语言能力事实上是人类学的学科要求。不管你做海外还是做国内的研究,参与观察都是人类学最基本的方法,不懂对方的语言是不可能真正 参与到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去的。人类学的学科规范上就有这一条,一定要掌握研究对象的语言。在海外研究方面,我记得我的导师高丙中教授说过,中国人类学只有走到海外去的时候,才能够从真正意义上遵循学科规范,也就是说,海外研究能够推动人类学科规范的建设。如果我们回自己老家做研究,你会对环境非常熟悉,似乎不需要长期调查就可以获取很多信息,而且也不用刻意学习当地语言。但是海外民族志研究一定要遵守学科规范,到海外就必须学当地语言,要全面了解那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当地的季节更替和社会活动必然是有周期的,我的导师当时就要求我们在田野点至少待一年,为什么呢?春种秋收是有周期的,围绕这个周期将产生人的各种社会活动的周期,此外还有生老病死的人生周期,对这些周期的观察需要较长时间投入。可以说,海外民族志研究实际上推动了人类学学科规范的确立和成熟,语言能力和田野调查时长(通常为至少一年)变成了硬性的要求。
具体说到语言能力的话,我们当然是希望做到听、说、读、写都要非常好。我自己当时的准备是不足的,我常说我当时去做泰国研究是先天不 足,是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大胆去做了。我去之前学了半年的泰语,当时的博士学制就是三年,过了博一就得准备出发,我是博二的第二个学期去到泰国,实际上时间已经很紧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准备。在泰国,因为待的时间比较长,我的泰语口语和阅读可以过关,但是用泰语写作还不行。之后要么用中文写文章,要么用英文写文章,没有太强的动力用泰文写文章。我后来见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迈克·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教授,他很厉害,他能用希腊语、意大利语和泰语写论文。他在课上会要求他的学生用对象国的语言写学术论文。他跟我说必须跟对象国的学者有交流,写作语言这方面要突破,他对自己和自己的学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推崇的方式。
那么,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何种语言能力?那就是能够用当地语言跟当地人非常顺畅地开展交流,能够阅读当地文献,最好能够运用对象国的语 言进行学术写作,跟对象国的学者进行观点交流。实际上语言是需要学一辈子的,不可能说我的泰语在做了两年田野之后就很好了,后面就可以一劳永逸,不是这样的。我自己感觉语言是没有止境的,你刚进入一个新的议题的时候,就会碰到很多新的词汇,你转过来做另外一个研究的时候又会发现很多新的词汇,实际上学习语言的过程也是你在寻找一条深入到研究议题当中去的路径的过程。比如说我刚开始在农村做调查的时候,接触到的很多词汇是关于乡村生活的,他们的宗教活动更多的是做仪式。但是后来我去研究曼谷中产阶层的修行实践的时候,人们很多时候不是在做仪式,而是在谈论、讨论,他们对佛教教义特别感兴趣。这时我就觉得他们谈论的东西我很陌生,我要从头开始跟他们学习,期间遇到很多比较艰深的词汇,包括他们用巴利文和佛教原典当中的一些词来讲佛教义理,我这时才对佛教术语有了新的认识。
冯:海外民族志学者的语言能力很多时候是从田野调查中培养起来的,这和课堂中的语言学习从内容到方式,存在哪些差异性?
龚:在田野当中学习语言与我们在教室里的课堂学习很不一样,当然课堂学习是前提。在去开展田野工作之前,学习语言一定是要“正儿八经”地 学,就是全面学习拼读的规则、语法的规则、书写的规则,这是很基本的要求。不能说简单学几句日常用语就可以了,一定要进行正规的语言训练,通过规范学习获得的相关语言能力是开展田野调查的基础。
到了田野当中之后,你会发现你学到的是“活生生的语言”,跟在教室里学到的印刷体的语言又不太一样。你会更多地看到语词怎样在一个情境 当中被应用,而它被应用的这个情境是非常值得去琢磨的。很多时候,语言的背后有一套行为逻辑或者是当地人的一套文化逻辑。我记得在泰国乡下的时候,我的房东第一次带我去寺庙。我就问她我们去寺庙是不是要带礼物。当时我的泰语不是很好,我不能很准确地表达那个词,我觉得去寺庙需要布施,布施的这些东西或许就是礼物,所以我就用了“礼物”这个词。我的房东说不对,去寺庙带的东西不是“礼物”,是做“功德”,她说“功德”不是“礼物”。那么,礼物是什么?礼物是人和人之间,普通人和普通人之间世俗的这种交换,而功德是在神圣场域发生的。二者在道德层面上完全不一样,一个是世俗的,一个是神圣的,有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在里面。我们在田野当中学习语言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词背后是有一套文化逻辑的,这需要我们慢慢地悟出来,在语言的使用当中,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用错了才意识到这个情境是什么样的,所以不要害怕犯错。
冯:您认为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的语言使用分为几个阶段?
龚:刚开始的语言使用是以满足个人的生存需求为目的的,你刚去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的问题、购物的问题、问路的问题。 语言学习会围绕自己很紧迫的、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去展开。但是到了研究当中,语言使用的场景就会转换。我下乡之前在曼谷待了一个多月,我要办一些手续,包括延长签证的期限,还要办一些访问学生的手续,因此在曼谷逗留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的泰语学习就进展很小,因为没有人跟我天天用泰语交流,我只是在办事的时候会用到有限的泰语。但是我到了乡下就发现生存是没有问题了,住在房东家里很安稳,但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就会慢慢地展开社会交往。这个时候的语言使用实际上是以观察的对象为中心的,我总想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在谈什么,在想什么,这个时候语言使用就不是以自己的生存为目的了,而是以了解周边的人为目的,我很迫切地想了解他们,他们也想了解我。
最开始我的泰语表达很差的时候,语言就成了一个障碍,他们问我问题我听不懂,我想问他们又说不出来,会存在这样一个情况,这是很正常 的,大家刚刚到田野当中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在语言没有那么顺畅的时候,你会更多地去观察别人在做什么。你没法直接问,不知道怎么问,你问了对方也听不懂,这个时候就得观察他们在具体怎么做,会在心里留下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没有人能够告诉你,或者告诉你你也听不懂,只能靠自己去观察。实际上这就是语言使用的第一个阶段,它是一个潜在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以观察为主。而通过观察获得的那种好奇感和心中生发出来的很多问题,是很好的田野调查的推动力,会推动着你去了解更多的事情。
第二个阶段就是开始积累一定量的词汇。我虽然听不懂,但是我会把听不懂的词记下,去查字典,听别人解释,各种听,慢慢通过滚雪球的方 式来拓展词汇和对于当地人的认知。我记得在田野调查中大概四个月后就能够跟当地人聊天,开始跟他们开玩笑,实际上这个时候语言就不是障碍了。结合自己的观察,和深入理解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文化,研究者对语言的掌握也变得越来越快,语言就成为很有效的沟通工具。
在更深的阶段我们要知道语言是在怎样的情境当中被使用。我想到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所的张慧老师谈到田野调查当中有不可言说的部分,以 及语言与文化不完全对应的现象。我们今天谈的是语言,但是语言的另一个方面是不可言说的那部分。我们在田野当中会经常碰到这种情形,有的事情人家是不会跟你明说的,要靠自己去体会,自己去领悟,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无法言说的部分往往是很有意思的点,也就是说并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说出来,社会生活中总有一些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要去体会为什么这个东西不可言说,在不说的情况下如何去微妙地表 达,这就需要我们绕道地去理解。你不能直接问,不能指望别人告诉你,你只有通过观察、通过猜测,通过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冯:在具体情境中使用语言,已经超越了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语言学的能力要求。
龚:对,很多时候你开始用某个词的时候是不知道这个情境的,当你用了之后,人家告诉你用的不对和应该怎样用的时候,你才会醒悟到为什 么会用错,那是因为我们从自己的这套文化逻辑出发去假设了人家的文化逻辑,而对方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理解的方式。这种语言能力的成长在很多时候伴随着文化的比较,我们在语言应用当中很多时候是在做文化的比较,或者是我们对当地的文化、对自己的文化要有一种反观的能力,这种能力跟语言能力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幽默,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要学会跟当地人开玩笑。如果你能够跟当地人开玩笑了,你的语言就基本上过关了。我做 田野的感受是,当我能够用泰语跟当地人开玩笑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比较认同我的泰语,而且他们会很欣赏这种幽默感。幽默背后的含义是值得去分析的。说到这里,可以从语言使用的角度去分析“幽默”在田野调查中有些什么含义。泰国人是很喜欢开玩笑的,我在那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也跟他们开玩笑,我发现如果你能跟当地人开开轻松善意的玩笑,他们就会非常欣赏你,而且他们会把你开的这个玩笑去跟其他人说,会说“茉莉(笔者的小名)那天说了什么什么”,玩笑就会变成人们的谈资。在这个过程当中当地人不是取笑你,而可能是很欣赏你。我在用他们的方式跟他们开玩笑的时候,当地人实际上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觉得我能够理解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反过来也更能理解我,它实际上是跨文化交流当中相互之间的理解都被加深的结果,而且也促进了相互之间的包容。如果我的学生去做田野调查,他们在那里能够跟当地人用当地语言开起玩笑来,我就会非常开心。这说明他们的语言学得很好了,而且真的能够融入到当地的文化当中去。
能不能学会当地人的幽默感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
冯:您除了去泰国做海外民族志研究,还去过荷兰、美国等国访学,在整个海外访学和研究过程中,学习泰语之外,您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语言 学习经历?
龚:我只正式学过英语和泰语。我在荷兰莱顿的国际亚洲研究所(IIAS)访学时,周围的人都能说英语,我的荷兰语只会很简单的几句。我于 2010—2011年在哈佛大学访学的时候,英语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实我的英语基础并不是很好,读博士期间又是到泰国做调查,英语并没有什么进展。我到美国访学期间,高丙中老师鼓励我在美国做一个调查,他说我们不能只了解东方,现在东方社会的很多理念和发展模式其实都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我们应该去看看西方社会的一些基本理念和社会制度,看看发达国家的社会构成是什么样的,这样我们在思考东方问题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比较性观点。他当时很认真地跟我说,要我考虑在美国做一个田野调查。
我一开始觉得这个挑战是很大的,但是我后来还是去尝试、去做了。我在美国波士顿的一个小镇上参与了很多公共活动,包括教会、社会团体 和地方政府的一些公共活动,可以说是大开眼界。可能学英语的年头比较长,到了那个环境当中进步比较快,但我总的感觉是我很难对着书本把一门语言学好,我更愿意在跟人的交往当中去学语言。当然每个人的语言学习路径都不太一样,至少对我来讲就是这样。我只有见到真实的、面对面的人说语言的时候,才能对语言有感觉。在跟活生生的人交往的时候,对方对某些词的有意思的运用会激发出我的想法,这时语言就成为了沟通的工具,也变成了丰富自己人生体验的工具,我对这门语言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在美国待了一年之后对英语比较有感觉,尤其是我参加教会的活动时,发现很多词都可以从《圣经》找到源头,这些词后来又演变成一些术语或者学术概念,如果不知道它的源头,我们会感到迷惑,但是知道它的源头之后就会发现这是他们文化里的一套东西。我没有什么很特殊的语言学习背景,我的感受是只有跟活生生的人去打交道,沉浸在那个社会当中的时候,语言才真的变成我的一部分,而且这个部分是很难忘掉的。我在泰国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的房东喜欢唱卡拉OK,他们就教我唱泰文歌曲,我当时学会的那几首泰文歌,歌词到现在都没有忘掉,张口就能唱出来,但是我回国后自己听会的一些泰文歌很快就会忘掉歌词。这告诉我为什么田野当中学会的东西忘不掉,因为它是生命的一部分,是我跟其他生命互动的一部分,它刻在生命的记忆里头,是很难被抹去的。
冯:您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是如何使用语言的?
龚:我当时的博士论文参考了一些泰文文献,但是这些文献比较局限在地方资料的范围,比如说关于调查点的地方沿革,我参考了当地乡政府整 理出来的文字。当时我并没有去借鉴用泰文发表的学术文章,这是很大的一个遗憾。泰国学者的英语一般都还不错,他们也很希望用英语发表文章,因此,我很多时候读的是泰国学者用英文写的文章。我在 2019 年出版的《佛与他者:当代泰国宗教与社会研究》当中有一些英文文献的作者是泰国人,但是泰文文献我还是参考的比较少。对我来说,我希望今后自己和学生能够更多参考泰文或对象国本土的学术期刊和专著,这是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因篇幅所限,省略文中的参考文献)
……
全文请长按识别二维码,前往中国知网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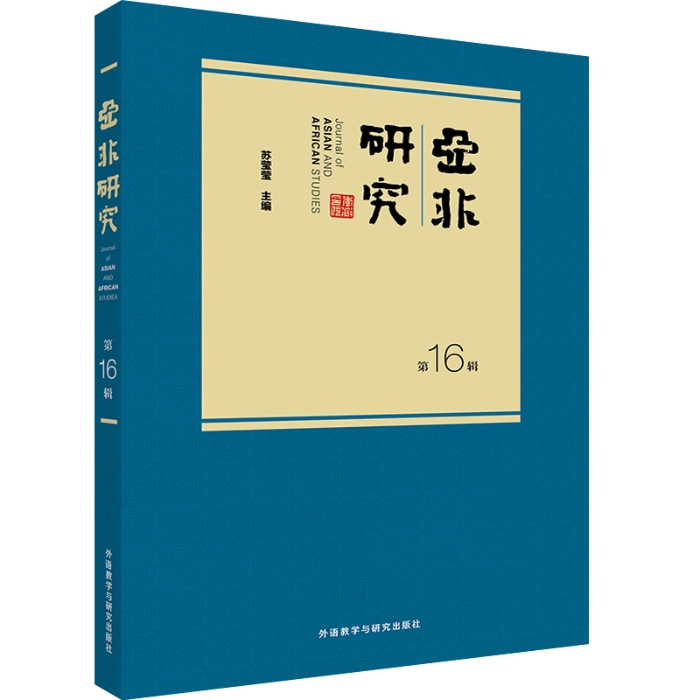
本文选自《亚非研究》第16辑
主编 苏莹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