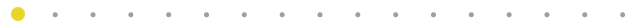纪念|贾洪伟:人在符号转换中的作用——对皮尔士与格雷翻译符指过程的批判与建构
【编者按】
作者简介
贾洪伟,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博士后、首都师范大学翻译方向硕士生导师、大同大学许渊冲翻译与比较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语言文化研究辑刊》执行主编、天外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川外国际话语体系研究院研究员、泰国西那瓦大学符号学与文化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等,兼任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翻译史研究会理事、“中国知网”国际出版中心翻译质检专家、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刊《语言与符号》编委、《符号学与艺术研究》主编等;研究方向为语言学、译介史、中国翻译思想史、海外汉学、翻译符号学、翻译安全、法律翻译等,主持省部级2项,参与省部级项目7项,国家社科一般项目2项、国家社会科学重要项目1项,出版专著5部、编著6部、教材2部,发表国内外核心期刊论文40余篇,普通期刊论文近50篇,与天外前副校长、中国符号学会会长王铭玉教授共同创建“翻译符号学”。
1.
引言
美国符号学家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 1834-1914)是美国本土创见最多、著述最丰、学科跨度最广的一位构建哲学系统的学者,兼通逻辑、数学、化学、物理等学科,故学术视角也最为宽广。上世纪70、80 年代,皮尔士的符号学和实效哲学(pragmaticism)思想传入国内,目前国内外学界对皮尔士实效哲学的关注有增无减,哲学界关注他从符号学角度探讨意义指称问题,符号学界侧重解构皮尔士符号学的理论思想,语言学界针对皮氏有关“玻璃质”和“黑匣”观点探讨语言的内在机制和本质,心理学界探索“黑匣”与语言生成和呈现的关系,翻译学界则着重于皮尔士符号学与翻译联姻的可能性以及能否利用皮氏框架建构翻译分析框架。虽然国内外有关皮尔士哲学思想的研究仍处于各领域的边缘地带,但皮尔士学术思想的重要性和价值逐渐凸显。
皮尔士三元符号关系就是符号(像似符—指示符—象征符和质符—单符—型符)—对象(直接对象—动态对象)—解释项(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终端解释项),与呈位—命题—议位、形式—本能—经验和一级符号范畴—二级符号范畴—三级符号范畴对应。按照皮尔士学说,符号—对象—解释项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无限的递归过程,即符号—对象—解释项这一三元关系中的解释项为新的三元关系中的符号,依此类推。从学术思想史角度看,皮尔士的三元符号思想对语言文化研究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 1901-1979)基于符号载体—所指—解释项三元观,构建符号表意的形式意义(符号与符号的关系意义)—存在意义(符号与所指的关系意义)—实用意义(符号与解释项的关系意义),而后形成了语言符号研究之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三大维度,突出了人在符号载意与转换过程中的作用(Morris, 1938: 3)。罗曼·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以诗学文本为切入点,将翻译划分为语内—语际—符际三大类别。荷兰符号学者兼符号翻译学家丁达·格雷(Dinda L. Gorlée,1943-)将三元符号关系、溯因—归纳—演绎三元推理逻辑、符指过程等思想运用于翻译过程及其相关现象和行为的研究。
纵观文献,皮尔士在讨论符指过程时弱化了人的作用,格雷虽然意识到这一现象,也设置了专门章节讨论这一问题,但仅局限于译者的角色,没能从符号学角度全面地剖析翻译过程中人这一要素的作用。本文拟从人这一要素出发,剖析皮尔士符指过程中人这一要素的相关思想,评述格雷有关翻译符指过程中对人这一要素的处理,最终从翻译符号学角度构拟人在符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2
皮尔士有关人这一要素的思想
皮尔士自1892 到1907 年期间一直关注人这一要素(Peirce, 1931-1966, 1979, n.d.)。为便于后文剖析,笔者按照时间顺序择要录入几例:
在引文(3)这一符指定义中,皮尔士明确地突出了人的作用,可见他并非无视人这一要素在符指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只是将人作为符号生成、使用和阐释的抽象主体来处理,但他没有将人纳入符号三元关系系统,可谓一大遗憾。与此同时,他更没有考虑符号转换这一特殊符指过程,此二端不免引发后人对皮尔士符号学理论解读,甚至会衍生后人对相关思想的误读,同时也不便于皮尔士符号学理论的传播。
3
格雷对皮尔士理论中人这一要素的解读与译者角色构建
世界著名符号学家、翻译学家丁达·格雷系现代国际学界首位以皮尔士符号学视角探讨翻译问题的学者,曾于1990 年在“意大利安达卢西亚符号学会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翻译即叛逆:论翻译符号学》(Traduttore traditore: semiotica de la traducción),提出了“翻译符号学(semiotica de la traducción)这一概念,尽管后来改称为“符号翻译学”,但对符号学与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二者的结合不断走向现代学科化。
格雷的博士论文“符号学与翻译问题研究——以皮尔士符号学为纲”(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1994),可谓是皮尔士符号学与翻译联姻的开创之作。格雷之主旨是从翻译过程及其相关现象与行为角度,解读皮尔士三元符号关系和符指理论,故以译者角色为切入点。她(Gorlée, 1994: 189)认为“作为交际者的译者具有双重角色,既要体现原语信息的受话者(或多位受话者之一),也要体现译语信息的发话者;既要体现阐释者也要体现发话者;既要体现阐释原始符号的受事,也要体现译语元符号的施事。从符号学角度看,译者承担指称与约束关系,因而垄断了翻译赖以生成的整个符号操控过程”。针对皮尔士理论中有关人的符号要素,格雷(同上)指出“对皮尔士来说,尽管符指过程属于三元过程,除了符号—对象—解释项,他没有明确地纳入第四个、第五个成分,但这并不是说:皮尔士不认可第四、第五任何一者的存在。”她进而做出如下三点归纳:(1)似乎皮尔士并未意识到发话者和阐释者均是人类个体,亦或甚至是具体人;(2)与符号生成者相比,貌似阐释者才是符号行为之根本,许多符号没有生成者(或发出者),或至少不是生发于任何个性化、下意识的符号创造;(3)译者头脑中的符号发出者与阐释者参与的是随着时间衍化的辩证关系,即一种半内部、半外部的对话,其中译者/ 符号发出者从属于译者/ 阐释者(同上:190)。因而,她据此认为:“符号行为与符号阐释未必一定受制于符号发出者与阐释者:皮尔士的符指过程是自我生成的三元符号过程。如同所有符号学范畴之符号一般,文本符号是积极地寻求通过某一阐释者实现自身(意义)的动态媒介,而不是如语言符号学的情形一般,消极地等待着被实现”(同上:190-191)。
针对格雷对皮尔士人这一因素观点的解读,我们认为有几点应该注意:(1)皮尔士并非没有意识到发话者和阐释者均是人类个体或具体人,前引文不但预设了人与人交流(具体非抽象)的施事与受事,还指出演讲者、作者、符号创造者及听众、读者、阐释者,更揭示了译者的两大准思维体(准发话者和准阐释者,于无形之中预示着1970 年代衍生出来的动物符号学),同时引文也蕴含着信息发出与接受过程总存在着以母语或社会母语为中介语的虚拟解读者,可见皮尔士并非仅局限于译者这一层面,反倒是格雷缩小了皮尔士对人这一因素的解读范围;(2)从翻译角度讲,许多符号无生成者或发出者是不符合翻译相关事实的,因为翻译行为是不可能没有原本的,即使是匿名符号发出者或伪作也一样具有文本符号的发出者,就连格雷自己也认为“一枚文本符号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先前、他者符号生成之物”(同上:221),这同样预设了人作为符号发出者或生成者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印证了符号乃人为生成之物,此可谓无人即无符号,更无符指活动和过程;(3)格雷也同皮尔士一样从抽象的理想语境出发,将译者角色分为两类(发出者与阐释者)不免落入传统译论的二元对立思想之藩篱,忽视了具体翻译类型带来的复杂性因素,原本的发话者与受话者,一旦落实到具体翻译行为中,还应存在前文提出的虚拟中介者,尤其是在中国佛经译场和大型翻译项目的合译中,还存在发出者—解读者(同阐释者)—录写者—润色者的多重关系,同时也隐含着虚拟的中介者因素,这是不应忽略的。
格雷将译者角色纳入契约性的符指过程,指出译者在翻译所在的契约性符指过程中具有符号发出者与阐释者、译者双重角色(即符号阐释者作为允诺人与符号发出者作为受诺人),作为当事双方,须履行契约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格雷忽视了几个问题:(1)法律契约系当事双方在共同意愿基础上订立的法律履行义务文书,翻译契约(translation brief)并非是发出者与阐释者之间订立的隐形契约,也不是译者两个角色之间订立的隐形契约,通常是由翻译赞助人委托给译者,当事双方签订隐形契约,且译者双重角色之间并不存在有形的契约文书,故而译者的行为只按赞助人或委托人提出的条件来完成,期间还可能因各种因素发生条件变更,从而就出现了翻译契约关系与法律契约关系之间的实质性差异。但从译事类型看,各类机构的专职翻译由上方交代任务,译者毫无选择,因而虽然符合法律契约特征的行为,可未必是自愿承担。佛经译场中担当各自任务的译者也未必有自由选择的行为意愿,但佛经翻译不仅符合法律契约特征的行为,且虽然出自个人自愿履行职责,却出自宗教情节,与法律契约的精神不是一回事,这是要区别对待的,不能笼而统之,故而格雷的有关翻译契约论断存在将复杂翻译关系简单化的倾向;(2)译者在翻译符指过程中时常因各种因素烦扰而出现带有动态性和感性化的阐释行为,这是法律契约与翻译契约的典型差异;(3)法律契约中的当事人不允许存在个性化的履行行为,而翻译则是典型的个性化契约行为结果,这是由言语行为的动态性、多变性、阐释无限性所决定的;(4)因委托人意图、译者意图、译文用途不同,各类翻译任务的契约条款、义务履行方式、最终取得的成果等均有所不同,如会议口译、视译、随同口译、交替传译等,法律翻译、政府公文翻译、广告翻译、文学翻译、外宣翻译等,转译、编译、改写、重译、自译等,落实到具体翻译实践中,所谓的翻译契约常常涉及诸多与法律契约不同的特征,这是不容忽视的。
虽然格雷在“翻译符指过程中的发话人与阐释者”和“翻译作为契约符指过程”两部分,均意识到人在(翻译)符指过程中的作用和重要性,但她只是在解构皮尔士的三元符号关系,解读皮尔士之所以隐去人这一关键要素之因由(其实,她只是引用皮尔士在几个场合提及人这一要素的观点,并认为皮氏并未考虑人的作用,而实质上应该是皮尔士以人作为符号主体为建构基础,说皮尔士没有考虑人这一要素,那为何出现对象和解释项呢?这似乎是格雷对皮尔士的误读),并未以此为基础,重构以人为要素基础的翻译符指过程,从而忽略了人在解释项生成过程中的重要性,也没能充分地在理论上构拟出翻译符指的真实面貌,没能指出翻译符指动态性、无限性、暂时性和多变性的真正根源所在。
构拟翻译符号学视域下人的作用
4
皮尔士符号学一直在强调符号—对象—解释项的三元关系,即符号意义生成于无穷尽的符号阐释之中,且符号之生命力就在于这种阐释过程,或曰符指过程。受皮氏影响,格雷也持同样观点,并将其用以阐释翻译过程及相关现象,提出翻译符指过程(translational semiosis),即“一个动态的、目的性的且非规约式(求知)过程”(Gorlée, 1994: 85),“旨在通过生成一系列解释项,呈现所指对象”(同上:166),“其中不存在让指称过程可确定性终了的终极或‘最终’解释项”(同上:85)。若没有人这一要素,不但不会出现符号,也不存在符号—对象—解释项这一三元符号关系和翻译符指过程。进而,皮尔士的三元符号关系必须以人为基本的存在前提,在人作为主体基础才能存在这一三元符号关系和翻译符指过程。基于前文有关二氏对人这一重要因素的处理及相关思想问题,我们尝试翻译符号学角度,构拟人在翻译符指过程中的脉络及其行为路径。
翻译符号学将以物理形式承载的有形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与非物理形式承载的无形符号(如思维、思想、构思等)之间的符号转换视为广义的翻译范畴,涉及同一语言内部、不同语言之间、语言与非语言之间、非语言符号之间的翻译行为。从翻译发生角度看,翻译行为涉及较多主体的角色与作用,如发话者、受话者、阐释者、翻译委托人/ 赞助人、虚拟中介者等,可见翻译符指过程不能脱离符号阐释主体而自发进行,故而负责阐释符号的主体——人就尤为重要。虽然皮尔士没有明确说阐释者尤为重要,但从皮尔士著述以及普通符号学的逻辑推理可知,且从皮尔士对解释项的重视程度也可以看出,在翻译符指过程中真正重要的是阐释者及其变换的相关角色,因为不论是符指意义的多变性、符指过程的延续性、符号表意的偶然性,还是文本符号的阐述和新文本的生成(虽然格雷没有这么说,但从格雷(Gorlée, 2010)的“元创作”的思想可推知:翻译文本的生成主要取决于符号阐释者),符号自身是无法完成的,必须由阐释者深入符号(文本)关系之中才行,这是符号乃是人为表意产品和工具这一宿命决定的。因而,翻译符号学不主张弱化符号行为主体——人这一关键性基本要素。
皮尔士将人这一要素做抽象化、理想化处理,格雷将人这一要素从皮尔士抽象化和理想化的神台上拉下来,落在了翻译符指过程中的译者角色上,不但尚不够全面且也囿于理想化的层面。翻译符号学拟将翻译符指过程中人这一要素分作抽象人和具体人,旨在突出人在具体翻译符指过程中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抽象人乃是普通符号学视阈下的符号创造者、使用者和阐释者,从宏观抽象的角度勾勒人的符号行为和过程;具体人乃是人类具体符号行为中的施事和受事,在翻译符号学中就是翻译符指过程涉及的符号发出者、阐释者、虚拟中介者等,涵盖传统译论(包括合作翻译、转译、编译)中的作者、读者、委托人、赞助人(委托人与赞助人有时合二为一)、译者等。故而,翻译符号学要在皮尔士符指过程基础上构拟人在翻译符指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就必须根据人在符号生成、解读和阐释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改写皮尔士的三元符号关系和符指过程,才能真实地反映翻译符指过程的全貌。
根据翻译符号学说涉及的现实情况,皮尔士之符号—对象—解释项三元符号关系,既可以改成以人为主导的人—符号—对象—解释项四元关系,甚至考虑更周到一些的多元关系,也可以改写为人与三元符号关系呈上下级层次的双重三元关系,即符号发出者—使用者—阐释者与符号—对象—解释项。就普通符号学而言,似乎后者在逻辑上、结构上和系统层次上更为明确。但是,要想将这一双重三元符号关系移入以解读和阐释为主要特征的翻译符指过程,似乎这一双重三元符号关系就势必要考虑到文本符号转换过程中符号主体的一系列变体要素,即文本符号发出者、文本符号解读者、文本符号阐释者和翻译文本符号产出者,其中因翻译活动类型不同,符号主体的角色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重合和交叉,自译过程中所有的符号主体(发出者、解读者、阐释者和产出者)为同一人,转译过程中的符号主体为原作者和第一译者共同担任的符号发出者与第二译者,编译过程中涉及的原文本符号发出者、作为符号文本整合的译者及真正意义上的文本阐释者,合作翻译出现文本符号发出者、文本符号解读者1(通晓原语文本者)与解读者2(基于前者的译本符号产出者)、文本符号阐释者1(通晓原语文本者)与阐释者2(基于前者的译本符号产出者)。
考虑到这些影响因素,格雷基于皮尔士的翻译符指过程似乎应该按照以人为主体作用的翻译程序,我们拟改写为三重梯度的四元关系,第一梯度以原作生成过程中的符指关系为参考,是翻译符指过程的始发点,故而是人1(原始符号生成者)—符号1—对象1—解释项1;再到以惯用语言(母语或社会母语)为中介语的解读和阐释过程:人2(原文本解读者,但不一定是译者本人)—符号1—对象2—解释项2;最后是译者(可能与原作者、解读者出现交叉或重叠)产出终端文本的过程:人3(可能与人1,或人2,抑或是人1 和人2 重叠)—符号2—对象3—解释项3。
可见,如果不充分考虑人作为符号主体的作用,以及在不同翻译类型中的活动过程,翻译符指过程乃至普通符号学中的符指过程,恐怕是难以实现的。不顾及人和活动类型这两个要素,一味地以理想状态为出发点,即使勾勒出翻译符指关系,恐怕也是缺少符号主体能动性、灵活性和复杂性的先天早产儿。与此同时,理想状态下的翻译符指过程也违背了符号赖以存在的阐释机制,不符合符指过程之无限性和多变性的规律和特征,因为这些均须以人及其相关的社会构成性背景因素为依托。
5
结语
本文以史为鉴、以历史文献为依据,回顾皮尔士三元符号观和符指过程中人这一要素的有关思想,梳理格雷对皮尔士有关人这一符号要素的解读与译者角色构建的观点,指出格雷认为皮氏“没有意识到发话者和阐释者均是人类个体或具体人”乃是对皮氏经典思想的误读,且有意地将皮氏人这一要素的指称范围缩小至译者层面,没能全面地反映出人这一要素在翻译符指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从符号生成和翻译之现实状况角度纠正了“许多符号无生成者或发出者”这一误读与理论谬误;从学理角度申明将翻译符指过程中的人局限于发话者和阐释者的二元对立思想,忽视了具体翻译类型(如合译)中存在的发出者、解读者、录写者、润色者等角色。
另外,以法律契约为参考,本文指出翻译契约符指关系中的当事人不等同于法律契约中的当事人,专职译者多为生存服务,并非完全出自自身的意愿订立契约关系,佛经中的译者虽出自意愿,但属于为宗教信仰服务,不完全符合法律意义上的契约特征,因而格雷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不但没考虑到具体翻译过程中译者因主客观因素出现的个性化言语行为,更没有兼顾到翻译符指过程具有的动态性、多变性、阐释无限递归性与法律契约过程之间的本质性差异。
笔者以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之间的转换为广义上的翻译界定,基于人在符号生成、使用和阐释中的角色和作用,将人这一重要的符指过程要素分为抽象和具体两类,并以皮尔士的三元符指关系为参照,将翻译符号学视域下以人(作者、中介者,以及或作者,或中介者合二为一的译者)为主导的符指过程,构拟为人—符号—对象—解释项为基础的三重梯度四元关系,以图为翻译符号学符指过程理论构建和应用奠定思想基础,与此同时也希望能对翻译符号学的构建和普通符号学本土化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