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人文研究 | 华劭:我的俄语教学与研究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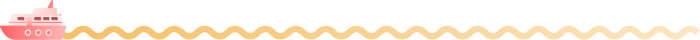
编者按
华劭(1930年6月13日-2020年11月5日),湖北汉口人,我国著名俄语教育家,杰出的语言学家。长期从事俄语教学与研究工作,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我国俄语教育事业,为俄语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等做出了卓越贡献。在新中国诞生之初,没有教材,他自己编写;没有老师,他自己求索。先生作为主要编者的《现代俄语通论》问世于 20世纪50年代末,是我国第一部现代俄语理论教材,开启了我国俄语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新时代。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先生不断开拓进取,在语言学理论方面辛勤耕耘、潜精研思。编著《现代俄语语法新编》(句法)(1979)和专著《语言经纬》(2003),由他领衔翻译的苏联科学院 1980 年版《俄语语法》(1990)都成为传世经典之作。丰硕的研究成果和广博的学术思想滋养和陪伴着我国一代又一代俄语学者的成长和发展,引领着他们一步步迈向自己事业的巅峰。
从1951年到2011年,60载教学与科研之路见证了先生为国育才的拳拳赤子之心!先生虽逝,文章留世功千古;桃李芬芳,教诲铭心传百载。先生德风千古!
1. 早年的教学工作(1951—1957)
1930年6月13日我出生于湖北汉口。1949年我考入华北大学参加革命,同年5月奉调进入东北联军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1951年初,我提前从哈外专毕业,留校任教,到1957年夏,我曾先后担任助教、语法教员、教研组长、《俄语教学与研究》杂志的编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我校经上级批准从上海、北京、东北、四川等地招收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学生,他们对教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时大多数俄侨教师并没有相应的知识准备,这样,满足这些要求的任务,就不得不由年轻的中国教师承担了。起初我们阅读一些能够弄到的苏联学校用的语法书,如谢尔巴(Щeрба)编的、马季琴科(Матийченко)编的语法,但很快发现它们并不适用于我国教学。于是,我们在俄侨教师协助下,针对一些学习难点,如前置词、连接词、不定代词、体的意义和用法,编写活页教材。虽然收到一定效果,但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勉为其难(с грехом пополам)地应对工作。随着来我校学俄语的人层次越来越高(学员中有国内知名大学的在校生、记者、高级翻译、甚至一些西语系的教授),学校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成立了独立于实践课之外的语法教研室、翻译教研室、编辑室;成立了研究生班。与此同时,哈尔滨外专成为高教部直属的外国语学院。作为语法教研室成员,我承受了作一个正规大学教师的压力。
大约1953年底,苏联专家乌哈诺夫(Г.П. Уханов)来我校执教,系统讲解语音学、词法、句法、历史语法,他还倡导搞科研,并在我校召开第一届全国俄语研究大会。我和许多同志一样,积极参加听课、讨论、做练习、看参考书,投入了很多精力,尤其是刚接触古俄语历史语法时,感到困难,花费不少工夫去弄懂基本知识。这些努力没有白费,后来我们学1955年版苏联科学院《俄语语法》时就感觉容易得多了。继乌哈诺夫之后,来我校执教的是以戈尔什科夫(А.И. Горшков)为首的一大批苏联专家(包括文学、普通语言学、词汇词典学、语法学、语音学、古俄语、古斯拉夫语教学法等方面的专家)。除给在学的研究生授课外,每位专家还培养几个脱产或不脱产的教师作为接班人。我被指定跟戈尔什科夫学习俄语语言理论,同时承担原有的教学与编辑工作。戈尔什科夫是维诺格拉多夫(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院士的研究生,对后者的观点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学习方式大致是先由他介绍某一课题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存在的争议,并指定阅读参考书,大家读后提出问题进行讨论,由他做总结。就我而言,最大的收获是提高了阅读俄语学术原著的能力。先后阅读的书有:维诺格拉多夫的《俄语》(«Русcкий язык»,1947)、沙赫马托夫(А.А. Шахматов)的《俄语句法学》(«Синтакси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1941)、佩什科夫斯基(А.М. Пешковский)的《俄语句法的科学阐释》(«Русский синтаксис в научном освещении», 1956)、格沃兹杰夫(А.Н. Гвоздев)的《俄语修辞学概论》(«Очерки по стилистик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1952)等。有些书是抱着词典、硬着头皮逐节逐章地啃下来的。另一收获是大致明白了传统语言学中有关俄语主要问题的研究历史和症结所在,为以后自己观察、理解、研习这些问题探明了方向,使我找到了研究的切入口和突破点。在这5-6年的学习、工作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理论学习对实际工作的重要性。在学校正规化的过程中,不同层次学生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广泛,加之在杂志编辑任内(我负责语言理论文章的审稿和答读者问专栏工作)要面对读者,甚至投稿作者提出的大量问题,我感到难于应对,凭自己理解或查阅资料做出的解答,未免肤 浅片面,就事论事,深感只有理论概括才能从本质上、系统地释疑解难。于是我所领导的教研组内,曾规 定每位教师半年读一本理论书,结合教学实际,做一次学术报告,互相切磋以提高教学和研究水平。在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借助苏联专家的帮助,1956年前后,在我校部分教师中掀起了一个学习理论小高潮,其中有些人学完副博士入学考试必读书目并准备答辩,后因1957年反右运动作罢。这段时间内,我对语言理论也产生了兴趣和学习愿望,广泛阅读有关书籍与学术期刊。记得1955年,当我们读到斯米尔尼茨基(А.И. Смирницкий)的几篇文章《词的分离性问题》(«Проблема отдельности слова»)、《词的同一性问题》(«Проблема тождества слова»)、《语言存在的客观性》(«Объективность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языка»)时,明显感到苏联语言学已开始引进一些西方观点,这引起大家的注意,也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当时,科技报刊提倡,要注意学术上的生长点,即那些有创意、有前瞻性、有价值的观点。我在读书时,也尽量去发现、搜寻自认为的所谓学术上的生长点。受科学视域和知识水平的限制,自己的判断难免偏颇、片面,但这还是有助于提高我的思考、领悟能力。在这段时间内,我还做了密切联系教学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少量论文,虽然水平有限,但由于有针对性,得到部分学生、读者和同行的肯定。与此同时,我积攒了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分设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简称高教部。一些读书笔记、例句卡片和为数不少的存疑问题,它们都有助于我以后的学术成长。
2. 赴苏联进修(1957—1959)
1957—1959年我有幸在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进修,进修的课程是普通语言学和现代俄语。我被编入俄语教研室,参加其学术活动。当时教研室主任为维诺格拉多夫院士,成员包括许多知名教授,如阿瓦涅索夫(Р.И. Аванесов)、库兹涅佐夫(П.С. Кузнецов)、洛姆捷夫(Т.П. Ломтев)、切尔内赫(П.Я. Черных)等。教研室指定加尔金娜-费德鲁克(Галкина-Федрук)教授为我的导师,帮我制定学习计划,并定期答疑。她要求以撰写论文来体现学习成果。语文系知名的普通语言学教师有布达戈夫(Р.А. Будагов)(我听完他的语言学引论课程),兹维金采夫(В.А. Звегинцев)(我选了他的语义学课程),列福尔马茨基(A.A. Реформацкий)(他主管语音实验室,不授课,为我们校正过发音,我向他请教过莫斯科学派的音位学说)。至于俄语本科语言理论课,由于此前已大都学过,我只选了洛姆捷夫的句法专题课,还听了维诺格拉多夫为教研室成员所做的专题讲座《俄语句法研究史》(«Из истории изуче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синтаксиса»)。1958年后应部分中国研究生和进修教师要求,校方为我们专门举办了系列讲座,由兹维金采夫主持,他本人为我们讲了词汇语义学,介绍了西方语言学知识,并邀请布达戈夫讲了“普通语言学”,切莫达诺夫(Н.С. Чемоданов)讲了“俄语历史语法”,伊万诺夫(Вяч.Вс. Иванов)讲了“印欧比较语言学”。我自始至终听完全部讲座。赵洵、赵云中等都是听课成员。此外,我和另一中国留学生一组,每周上两小时俄语实践课和两次德语课,学习条件很好。
除听课外,我参加了一些学术活动,如旁听1958年莫斯科举行的第Ⅵ届斯拉夫学大会,兹维金采夫新书《语义学》(«Семасиология»)的讨论会,以及关于“生成语法”的讨论会。此外,还旁听了一些博士论文答辩会,我记得起来的有阿赫玛诺娃(О.С. Ахманова)关于词汇学—词典学论文答辩,杨科-特里妮茨卡娅(Н.А. Янко-Триницкая)有关带-ся反身动词的论文答辩,我参加这些活动获得了新鲜信息,增长了一些知识。
我主要是在国立列宁图书馆自学,阅读与我感兴趣问题相关的专著和研究生的存馆论文,然后带着产生的问题向专家或导师请教,每隔两周去导师家一次。有一段时间我从早到晚泡在图书馆,记读书笔记,撰写文章,生活紧张、单调。那时,列宁图书馆经常举办一些学术活动,我有幸买过一次听文学朗诵的长期联票(абонемент)。记得先后听过阿赫玛托娃(А.А. Ахматова)朗诵自己的诗,人民演员伊林斯基(А.И. Ильинский)朗诵契诃夫的小说,某朗读名家朗读的保斯托夫斯基(К.Г. Паустоский)的小说。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另一桩我高兴做的事情就是逛书店,特别是旧书店(Букинистический магазин),从那里我弄到1933年俄译版的索绪尔(Ф.де. Соссюр)的《普通语言学教程》(«Курс обще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万德利耶斯(Ж. Вандриес)的《语言》(«Язык»)等书。这些书对我学习普通语言学有很大帮助。
我当时萌生兴趣并尝试研究的问题有:词汇学—词典学方面斯米尔尼茨基-阿赫玛诺娃(Смирницкий-Ахманова)提出的《词的同一性与分离性》(以及由此派生的词作为语言集合单位的界限问题);词法方面的《不同类别语法范畴的性质差异》;句法方面则是由逻辑—语义构成的句子类型及其 教学;与言语教学密切相关的句子实际切分。在普通语言学方面,则更多是了解有关索绪尔的学说,获取有关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信息。
3.“文革”前的教学与科研(1959—1966)
从1959年回国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断断续续地做过一些教学和研究工作。1959年秋回黑大后,曾被短暂安排在《俄语教学研究》杂志任编辑。很快,因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被认为思想认识跟不上国内形势发展,被下放修建水库和到我校农场劳动,前后达两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因中苏关系恶化,自然灾害频仍,下乡办学导致我系大批师生患浮肿病,俄语教育事业元气大伤,我任职的杂志也停办。后因落实广州会议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我被从农场召回教书,主要给研究生班及来我校的进修教师讲授词汇学、句法学,还指导一名研究生撰写论文《论词义发展中的通感现象》,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工作。此外,我还在本科讲语言学概论和实践语法课,我按在苏联进修时形成的句法观念,在高年级尝试按句型教学,收到一些效果,我就是以当时的讲义为底稿,后来编写了1979年出版的《现代俄语语法新编》(下)(商务印书馆)的句法部分。此外,我参加了1965年出版的《现代俄语通论》(商务印书馆)的编写工作。在科研方面,由于受当时条件限制,很少接触俄国的(更不用说西方的)学术思想,我写的一些文章,多半是拓展以前在苏联进修时形成的想法,如《试论俄语名词数的范畴》(1962)(它和此前发表的《论俄语体范畴》和未发表的《论形容词的比较级范畴》都是苏联进修时撰写论文的组成部分)、《俄语中的数量句型》(1963)、《试谈句子的实际切分》(1965)。后两个问题也源于以前萌生的思想,并在以后的年代成为我关注的对象。我始终认为,随着认识的变化,对从事的研究课题应该持续深入地研究,不宜浅尝辄止、见好就收。1965年下半年我奉调参加呼兰县农村“四清”运动,结束了相对稳定的教学生活,直至翌年8月,我被召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并由革命动力变成革命对象,卷入“文革”的动乱,中断了教学研究活动。
4.“文革”期间的教学与科研
“文化大革命”是疾风暴雨式的,大家先后经历了大批判、派系战斗、清理阶级队伍,教学活动基本上停顿了,部分教工长期下放农村。我和一些教师带领尚未分配、滞留在校的学生下乡办学。当这些同学离校后,人散楼空,学校甚至因无经费停烧暖气。在这种严峻的条件下,自然也就无人问津学问了。我在校内挖了一阵防空洞后,被派往铁力县深山老林中修战备基地,作为战争爆发时学校迁往的地方。直到1970年代初被召回学校,为招收工农兵学员做准备。回校后,由我提出,学校批准编写《现代俄语语法新编》。书成之后,因政治形势变化,审批手续复杂,直至1979年才出版。此书反映了我当时的认识和教学经验,力图满足学生实际需求,鼓励学生自己探索发现一些模式、规则,主张所谓开放式地学习语法,书中也提出一些不无争议的观点,例如,“不同语法联系与句型的关系”“从意义出发研究展词联系”“单句的繁化与复句的简化”等。书出版后,得到一些同行的肯定,且多次印刷,但也有非议,主要是无法与现行教学体系兼容,与现行统一考试标准不符。迫于压力,我把准备好的有关实际切分的材料去掉了。那时我就体会到,想在教学改革、观点创新上有点进展是不容易的事,需要有勇气和毅力。“文革”后期,我参加的另一有学术价值的活动是编写《大俄汉词典》,任务是中央交代的。我在苏联留学时期,曾接触过一些词 汇学、词典学理论,对编写工作产生一些兴趣。除参加撰写、审校、讨论词条外,我还负责编写虚词部分的词条。在工作中我认为词典编纂学有三个主要的理论问题,一个是所编纂词典的目的和功能决定了词 典的收词范围,即确定收词的时间界限(收不收以及收哪些古词、旧词、新词),空间界限(收不收以及如何收方言词汇),社会界限(收不收以及如何收只用于少数或部分社会团体的语言,如行话、科技术语、俚语、黑话等)可简称之为词典的界限;其次是词条内容的界限,详见阿赫玛诺娃《普通词汇学与俄语词汇学概论》(«Очерки по общей и русской лексикологии»)及《语言经纬》一书的相关部分;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问题是释义问题,现行的无论是以同义词、反义词释义,转说释义,翻译释义,构词派生或语义派生释义都有其天生的缺点:未揭示词的语义内涵,只是指出其等义词语及词义产生的来源和方式,这也是蓬勃兴起的语义学所致力解决的问题。
5.改革开放初期的教学与科研
“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全面(包括学术界)改革开放时期,整个俄语学界也面临全新的局面。我国开始摆脱将近三十年与西方学术界隔离的状态,着手恢复并增进了解我们所研究语言母国的学术发展状况。禁锢的闸门一旦打开,各类信息蜂拥而至,如功能语言学、结构语言学、生成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语言哲学不同的思潮,新颖的观点,陌生的术语令人眼花缭乱。随着与苏联学术交往的扩大与加深,逐渐发现,我们师长辈苏联老一代语言学家已慢慢成为过去,与我年龄相仿的一代学者,其中不少人原来是研究西语的,已占据了俄语语言学学术界的中心舞台。像梅利丘克(И.А. Мельчук)、阿普列相(Ю.Д. Апресян)、阿鲁秋诺娃(Н.Д. Арутюнова)、帕杜切娃(Е.В. Падучева)、斯捷潘诺夫(Ю.С. Степанов)等学者的名字在20世纪50年代是很少有人知晓的。这段时间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新知识,我参加了《国外语言学》和中国俄国教学研究会举办的一些学术活动,增长了不少的知识,但主要还是靠自学。记得当时我们从学校图书馆、资料室翻出尘封已久的上述苏联学者的著作和论文,包括从校外和苏联同行那里弄来的书,大家再一次找回20世纪50年代学习的劲头。不过这次没人指导,只能依靠自己琢磨、同行切磋。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格局对教学与科研提出新任务。恢复高考初期,我校招收了一批有相当俄语实践能力和一定理论基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不少后来成为有成就的学者、教授。以后又正式招收攻读硕士学位(自1985年起)和博士学位(自1987年起)的研究生。为研究生授课和指导论文给我们的压力很大,我一直是竭尽所能、边教边学,与同行、研究生互教互学。大概到1990年前后,研究生教学才走上轨道。概括说,当时的形势要求我们掌握新知识,迎接新任务。
改革开放初期阶段,在教学上我做了几桩事:一是参与招收硕士生、博士生筹划工作,包括制定培养计划、提出招生要求、讨论课程设置、论文撰写形式、答辩程序等等;二是为研究生先后开设了普通语言学、句法学、历史语法等课程,并指导三名硕士生,协同指导一名博士生撰写论文、攻读原著;三是跟兄弟院校进行学术交流,应邀讲学,参加答辩。1985年在高教部中国俄语教师研究会组织的学习活动中,我与另两位同志,为中青年教师较系统地介绍苏联1980年《俄语语法》的特点。我负责讲解句法部分,着重介绍了原书作者所持的新观点,如语言与言语相互关系,语言单位及其变体、句子的类型及其聚合体等等,还涉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在语言研究方面,基本上是结合教学体会与学习心得写了一些文章,其中也包含一些自己的见解。有些论文是为学术会议撰写的报告:《有关俄语句子实际切分问题》(1983,重庆)、《关于语言单位及其聚合关系与组合关系》(1985,哈尔滨)。其余的文章有涉及语义学的,如《用于句子转换的词汇手段》(1991),语用学方面的有《从语用学角度看回答》《说话人与受话人》等,以及一些评介性论文。也许值得一提的是论文《俄语教学改革之我见》,至今我仍然认为其中的一些主张有现实意义,尽管它并未得到同行的广泛认同。另一有实际价值的工作是信德麟、张会森和我缩写合编了苏联科学院1980年出版的《俄语语法》(1990),该书至今已多次印刷并再版。
6.重返苏联
改革开放以来,我曾三次重返苏联。第一次是1985年,我作为高教部组织的“中国苏联教学考察团”成员之一,参访了苏联高教部、首都和地方的一些大学,了解他们的俄语及外语教学。在普希金学院见到了过去的导师戈尔什科夫,但囿于当时政治形势,未能深入交谈。给我总的印象,那里的教学还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至于学术开展状况,由于时间紧迫,基本上无法了解。第二次是1990年,去莫斯科参加世界俄语语言与文学教师联合会的大会。这是苏联解体前盛况空前的一次大会,会上会下与同行交流,获得不少信息,并弄到一些资料和书刊。会议期间我在克林姆林宫被授予“普希金奖章”,并获得机会以校友身份翌年重返莫斯科大学访学一年。1991年初我自费购车票到莫斯科大学,到校后,发现学校大变,校园荒芜,管理混乱,后来我还见证了“8.19事件”,以及其后续的大游行、莫斯科大学共产党党委办公室被查封并被迫离开学校一类匪夷所思的现象。我在教研室报到后,除给我指定一位联系导师外,基本上就不管我了。这样也好,我有了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普通语言学、语义学、篇章语言学上,特别放在我先前已有初步了解且感兴趣的学者的学术观点上。除了阅读大量在图书馆、旧书店获得的有关书籍、论文外,我抄录、影印了一些学术资料,其中包括1985年维也纳出版的梅利丘克、若尔科夫斯基(А.К. Жолковский)《详解组合词典》(«Толково-комбинарный словарь»)。这些资料对以后的教学、科研工作有很大帮助。这一年我还拜访了一些学者,如时任俄语研究所所长的卡劳洛夫(Ю.Н. Караулов)、句法学家佐洛托娃(Г.А. Золотова)、心理语言学家列昂季耶夫(А.А. Леонтьев);参加了一些学术会议,如讨论《俄语现状及俄罗斯学发展中的问题与前景问题》(1991年5月,在科学院俄语研究所召开)、语言逻辑分析问题小组召开的当年例会,这次例会上许多著名语言家作了报告,且有逻辑学者参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主持人阿鲁秋诺娃关于《有关行为目的的概念》(«О понятии цели действия»)的报告,思想深刻、充满哲理。此后我就搜集阅读她的著作及有关语言逻辑分析的丛书。这一学派和以梅利丘克、阿普列相、帕杜切娃为代表的语义学派以及斯捷潘诺夫的普通语言学观点都给我以后的教学和研究不少启迪。
7.晚年的俄语教学与科研
回国后不久,我被国家学位委员会正式核准为博士生导师,我的工作重点逐渐朝这方面转移。我先后 指导了6名博士生,包括普通语言学、篇章语言学、语义学、句法学、语用学等研究方向的学生,为他们指定参考书、答疑、并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培养博士生的过程也是自己学习提高的过程。这些博士生都已先后成为学者、教授、博导、教学骨干和领导。他们和另外一些年富力强、有见解有作为的老师,逐渐取代了我们这一代人。
进入21世纪后,我已年过古稀,不能再带研究生,只是做咨询答疑、审阅论文,主持答辩一类辅助性工作。不过我还继续为研究生讲两门课。晚年我有幸与进我校博士后流动站的老师从事合作研究,他们进站时已学有所成,对所研究的课题(分别是语气词和语义动态发展)持有自己的见解,我只是在自己能力所及范围提供一些参考意见。这两位老师现在均系教学骨干,还与我保持信息交流。新世纪前后,我结合教学与学习心得撰写了十几篇文章,其中一部分收入《华劭论文集》。2003年我出版了《语言经纬》一书,该书被高教部推荐为研究生阅读参考书。
我从1951年开始执教到2011年完全退出教学舞台,回顾一生感慨良多。现在的俄语教学与科研情况,是20世纪50年代初无法想象的。为此做出贡献的我的前辈和同辈老师(有些已不在世),他们的业绩值得我们怀念、铭记。我是这段时间——俄语事业艰难发展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来源:《欧亚人文研究》2021年第一期
责编:蔡晖
投稿邮箱:oyrwyj@bfs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