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俄语,教书育人:两代人的初心坚守——李英男口述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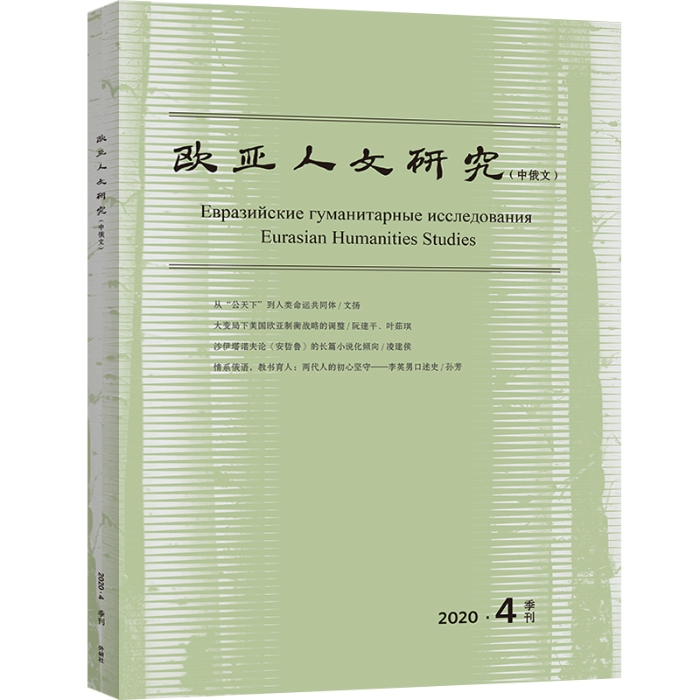
提要:李英男出生在一个不平凡的家庭,其父李立三是我党早期著名革命家,其母李莎是老一辈的著名俄语教育家。母女俩都曾执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她们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兢兢业业,桃李芬芳,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俄语人才,为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俄语教育;李莎;李英男;口述史

李莎(1914—2015),原名伊丽莎白·帕夫洛芙娜·基什金娜(Елизавета Петровна Кишкина),中国籍俄罗斯人,我国早期著名俄语教育家。她是已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全国人民防空委员会秘书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先生的夫人。李莎出生在俄罗斯萨拉托夫省,1941 年毕业于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先后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曾任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俄友好协会理事等职,系中国老教授协会名誉理事、全国政协委员。曾多次受到俄罗斯联邦和国际俄语教师联合会的嘉奖,并获颁勋章。
李英男(1943—),李立三和李莎之长女,我国当代著名翻译家、俄语教育家、博导,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院长、北外俄语中心主任;曾任北京市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委员;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委员;2002 年至今担任中俄友好协会常务理事、顾问。2006 年获俄罗斯联邦国家奖章“普希金奖章”;2009 年获世界俄语教师协会普希金银质奖章;2018 年获俄罗斯外交部国际合作署“友谊与合作”荣誉奖章;2019 年荣获“中俄互评人文交流领域十大杰出人物”称号。主要论著:《俄罗斯历史之路——千年回眸》(李英男、戴桂菊著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民族意识》(李英男作 . 俄罗斯研究 . 2002 年第一期)、《哈尔滨俄侨诗作中的中国形象》(李英男著 .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等;主要译著:《我的父亲毛泽东》(李英男,刘霞译 . 外文出版社,2004)、《牡丹亭》(李英男译 .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元曲选》(李英男,谢尔盖·托洛普采夫译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等。

李莎照片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1、李莎的哈尔滨记忆(1946—1949)
1946年,年轻的李莎追随李立三来到中国,开始了全新的异国生活。她踏上中国土地后到达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哈尔滨。这是个俄罗斯味十足的边境城市,语言障碍相对较小,李莎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并开始了在这里的教学工作。
李莎抵达哈尔滨的第一天,便结识了一位面容端庄、举止文雅的年轻女性,此人虽身着中式棉布旗袍,却能说一口纯正、流利的俄语,让李莎觉得“和俄罗斯人讲的毫无两样”(李莎,2009:174),这就是李莎后半生中最亲密的知己赵洵。与赵洵的缘分和友谊使李莎得以投入到党的俄语教育事业中,成为众多俄语人才的培育者。
中国共产党的俄语教育是从1941年在延安开始的,当时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三分校成立了俄文翻译大队。1946年哈尔滨解放,俄文翻译大队的部分成员受命前往哈尔滨创办俄语学校。是年11月7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正式成立,位于哈尔滨市的马家沟,由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直接领导,属军事院校,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兼任校长。当时苏军还没有完全撤出哈尔滨,需要经常和苏方进行联络,所以这所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是顺应时局的产物。1948年,它更名为“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转交给东北人民政府领导,简称哈外专。(阎明复,2015:98)
据李莎回忆,由于刘亚楼将军有各种头衔,公务繁多,所以实际负责哈外专工作的是两位女性,一个是王季愚,一个是赵洵。王季愚后来成为校长,赵洵是副校长,她们两位都会俄语。特别是副校长赵洵,她出身于爱新觉罗家族,从小在俄语环境中长大,俄语非常地道,算是第二母语。后来她参加革命去了延安,1946年从延安回来,到哈尔滨之后就被安排到这个学校做管理工作。李莎是学法语的,毕业于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她很喜欢自己的专业,刚到哈尔滨的时候,她本想做些法语翻译工作,但好朋友赵洵推荐她到自己任职的学校当俄语老师,于是李莎从1947年初开始就进入前面所说的“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也就是后来的哈俄专任教了。
在李莎的记忆中,当时的学员们穿的都是学校统一发放的黄色军装,住在集体宿舍,纪律方面管理较严。班级都不大,李莎教的第一个班只有10个人左右。校舍用的是日本人留下来的营房,没有供暖设备,不过大家自己动手清理打扫得比较干净,也简单地粉刷了一下。王季愚和赵洵都非常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由于那时候整个供应条件都比较差,学校在郊区建了一个自己的农场。农场里不单种菜,还养鸡、猪、牛,保障学员们有蛋吃、有肉吃,这大大地改善了学员们的生活。两位女校长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非常平易近人,与学生们建立了朋友般的关系。
那时候哈尔滨的俄侨不少,哈俄专聘请了一些学历和文化修养比较高的担任外教,这样就保障了实践课、口语课都是由一些俄语比较地道的老师们授课。那些俄侨老师都被当作专家对待,工资标准定得比较高,但李莎去了以后赵洵却把她的工资缩减了一半。一开始李莎对此有点不理解,后来听了赵洵的解释才明白:“你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外籍老师,你是中国领导干部的家属,是我们自己人,所以不能搞特殊。”(李莎,2009:175)这件事非常典型地体现了那个时代共产党人的做事原则。李莎欣然接受,并开始认真工作。
最初在教学方面李莎还没有什么经验,好在她的文学功底很扎实,是个俄罗斯文学爱好者,从小读了很多书,另外在大学期间她上过教学法的课程,对外语教学法有一定了解,这给了她很大帮助。李莎非常热爱教育事业,热爱自己的工作,很愿意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一心想要把学生教好。她回忆说,那个时代的学生都非常认真,他们都是一心一意学习,“党要求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都把学习当作一个革命任务。李莎教的第一个班里后来出了不少人才,包括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翻译阎明复、外贸部部长郑拓彬等。特别是阎明复,他后来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就在李立三的领导下,所以跟李家关系也一直比较密切,也非常关心李莎老师。还有其他一些优秀的学生,他们一直跟李莎保持着联系,这让李莎非常高兴。
哈尔滨的那段工作和生活给李莎后来的俄语教学生涯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是一段难忘的开始。

李莎全家福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2、李莎的北外教学之路(1949—1996)
1949年春天,李立三全家从哈尔滨搬到了北京。刚到北京的时候李莎还没有工作,但是她坚定地认为,女人不能只待在家里“相夫教子”,还应当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实现自身的价值,于是她决定继续工作。1949年底,她几乎是同时接到了北京俄文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的任教邀请函。第一个学年她同时在这两个地方教课,可见那时候俄语专家还比较稀缺。
当时的北京刚刚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俄语教育事业正处在恢复过程之中。启动较早的是北京大学。北大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就开设了俄语班,不少参加革命的同志都在那里参加了学习。但是后来发生战乱,日本人侵占北京,国民党统治陷入混乱,俄语专业就荒废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著名的俄罗斯文学专家、翻译家曹靖华教授被任命为北大的俄语系主任,他想复兴和发展俄语专业,非常重视师资队伍建设。于是他找到李莎,聘请她去上课。曹靖华教授的俄语纯正,学识渊博,与高尔基等一批俄苏作家、文艺理论家保持着亲密友谊,曾被聘为列宁格勒大学的教授,在苏联的名望很高。(李莎,2009:226)李莎对他非常钦佩和敬仰,也很感谢曹先生的邀请和器重,所以就答应在北大兼课。然而,李莎对在北大的授课有些不太适应,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时候的北大还保留了早期的办学体制,即模仿西方的自由选课制度,没有固定的班级,学生可以来,也可以不来,所以作为老师不好掌握学生的出勤情况。而李莎早已习惯了苏联高校的教学模式,班级固定,教学安排中规中矩、作业布置井井有序。于是,在北大兼职不到一年,李莎便向校方提交了辞呈,之后,她就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俄专的工作上了。
这个“俄专”就是北外的前身,全名叫北京俄文专科学校。解放战争时期,中央翻译大队从延安出来的时候兵分两路,一部分跟着大部队奔赴东北,留在哈尔滨,而另一部分在华北地区周转了不少地方,在石家庄成立了华北联合大学,后来又组建了华北大学,1948年6月为迎接全国解放专门在石家庄成立了外事学校,所以进北京的时候,这个俄专的骨干都是从石家庄那边过来的。据李莎回忆,当时有俄语专业的教学单位比较少,除了北大和俄专就没有其他的学校了。而后者是一所不对外公开招生的内部学校,在中央的领导下,专为中央机关和部队培养俄语翻译,带有一定的保密性质。俄专最初由中央编译局主管,属于同一个编制下的两个单位,俄语翻译家师哲既是编译局的局长,也是俄专的校长。学校的校址最开始在西城区,离编译局很近。学校是军队编制,准军事化管理,实行供给制,发军装、包伙食。一开始,学校还没有自己的食堂,学员们都是列队步行到编译局的食堂里吃饭。后来两个单位就慢慢地分家了,师哲的副手张锡俦被任命为校长。50年代初,学校更名为北京俄语学院,在西直门外的魏公村开始兴建新校区,1955年学校完全搬到了新校舍。当时只有东院是俄语学院,西院是另一个单位,叫外语学院。外语学院规模小一些,简陋一些;而东院建了主楼,中间是操场,两边是学生宿舍楼。一开始,学校并没有单独的礼堂,各种活动都是在食堂里举行。
最初这段时期,李莎在北外的工作紧张而充实,每周课时多达24节。那时候的中苏关系非常好,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中国表现得更开放、更友好,各方面的关系更密切了,来中国的苏联专家也多了,所以50年代中期迎来了俄语专业发展的高峰时代,全国的外语教学是以俄语为主,英语被排挤到比较边缘的地位,俄语教学的规模达到历史高峰。在李莎的记忆中,那时候的学生人人都很自觉,都愿意学俄语,而且非常热爱俄罗斯文化、俄罗斯文学。那个阶段李莎的教学任务主要就是给学生们上精读课,包括低年级的发音课和高年级的口语课。后来,李莎还为大学老师进修班和留苏预备部担任过任课老师,给很多已经在岗的俄语教师和准备赴苏留学人员进行培训,也参加了北外自主建设的第一套教材“老八本”的编写和审定工作。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友好的时候,很多苏联专家带着夫人来到中国,这些专家夫人们有很多来到北外当外籍教师。尽管她们之中学外语教学的比较少,但大部分对待工作很认真、很热情,所以她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学校的师资力量。学校也聘请了一些正式派过来的苏联专家,都是学过语言学、搞文学研究的老师,尽管人数不多,但起到了骨干作用。那时候学校的规模已经发展到在校生约四五千人,仅苏联外教就能达到八九十人。后来,上外和其他各地的高校都开设了俄语专业,大部分理工科大学的公共外语也都开设了俄语,中学也是以俄语为主,所以俄语的师资需求很大。北外当时虽然毕业生很多,但都能找到工作,都能发挥作用。然而 60 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突然撤走了所有专家,俄语教学受到了巨大打击。当年的毕业生突然就没有出路了,要出国留学的学生也不去了,只能重新分配,包括已经在高校或中学当老师的人,都只能赶快转行搞英语。对北外来说,由于是全国的俄语教学中心,而且是在外交部的领导下,所以要保留俄语专业,保证俄语教学继续进行,但大幅度压缩了教学规模。1959 年东、西两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外国语学院(1994 年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就变成了俄语系。
这段时期,李莎始终坚守在教学岗位上,一直正常上课,完成教学工作。1963 年,本来早已不再给低年级上课、只承担高年级教学的李莎,主动要求到一年级,给一些来自边远农村的工农兵学生上课。因为她觉得这些孩子非常可爱,很淳朴,求知欲很强,她很喜欢这些学生,觉得跟他们在一起非常愉快。这些学生里有的后来还成为了大使,比如姚培生。那时候苏联专家都被撤走了,夫人们也都跟着走了,外籍教师所剩无几,除了李莎以外,也就还有两位有俄罗斯血统的中国老师,好在 50 年代教师进修班培养出来的那一批青年老师们已经成长起来了,个个都成了教学骨干,也能够担当起重担了。
后来的“文革”迫使李莎不得不中断了自己的教学工作,十三年后她重新回到北外,又继续投入到自己所钟爱的教书育人事业中,直到 1996 年被病魔击倒在讲台上。如果说在哈尔滨俄专的短暂两年是李莎教学生涯的初期阶段,那么后来在北外的几十年就是李莎为自己所钟爱的事业努力奋斗的宝贵时光。她把教室当成自己实现人生理想的阵地和守望收获的田园,学生的每一点进步都让她无比欣慰,她不仅在课堂上尽量鼓励学生,待他们一视同仁,而且在课下主动与学生拉近距离,把他们当成朋友。她的默默耕耘和辛勤付出换来了学生们对她的无限爱戴和高度评价,无论是中国学生还是越南学生,都把李莎当作尊敬的老师,甚至是亲爱的母亲,在心中长久地铭记着她的教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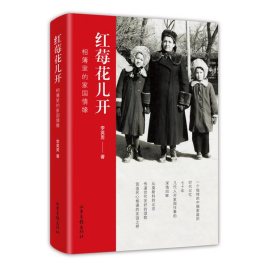
李英男所著书籍,讲述一个家庭与中国的缘分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3.李英男与北外的缘分(1974至今)
李英男于1960年在莫斯科读完中学,当时李莎非常希望女儿能留在苏联继续学习,进入莫斯科大学攻读学位。可是,年轻的英男特别想家,觉得自己应该“在中国定居,不想离开中国,我就应该是中国人”(李英男,2019:107)。于是,尽管妈妈有些失望,李英男还是执意办理了回国手续,在1960年秋天回到北京。李英男刚刚回国的时候,最初的梦想是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但后来发现中文知识如同浩瀚大海,自己难以达到要求,于是改变了志愿,决定发挥自己天生的优势,以外语为专业。
1962年,李英男考入北外,成为西班牙语系的一名学生。她很喜欢自己的专业,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并且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努力融入校园和班级,用自己的行动消除了文化背景的隔阂,最终使大家不再视她为“洋小姐”,而是把她当成了“自己人”。遗憾的是,不久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北外学生全部停课了,除了毕业生,其他的都留校“闹革命”。李英男的学业也受到影响,只能暂时中断。1967年,父亲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母亲被关进秦城监狱,李英男和妹妹也被关进牢房,不得不独自面对生活的考验。1970年,李英男被安排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跟西班牙语系一年级的同学们一起在农场锻炼。两年后,国家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重启,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想到需要储备年轻的外语人才和外语干部。于是,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湖北干校的北外学生在1971年9月回到北京,李英男也跟着回到了北外。
那段时间的李英男曾对未来非常迷茫,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安排,好在命运之神眷顾了她,使她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方向。1974年,李英男开始到北外俄语系工作,这既是组织的安排,也是她与俄语系的缘分。俄语系的老师有不少是李莎的学生,尽管李莎受到迫害被关进监狱,后来还被送到山西,但他们并未视她为敌人,而是常常向英男问候她的情况。当时俄语系比较缺乏母语为俄语的老师,据李英男回忆,当时只有两位在苏联长大的中国老师母语是俄语,但是她们二人身体都不太好,所以副系主任程立真老师便向李英男发出了诚恳的邀请。李英男高兴地接受了这份宝贵的邀请,实现了留在北外工作的梦想。
李英男到俄语系工作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新招的工农兵学员上口语课。当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甚至开始备战了,所以一下子就招了10个班的学生,总共约150人。李英男给这10个班上口语课,每个班2课时,加起来就是20课时,所以每天下课后都觉得口干舌燥。然而,在俄语系的工作却让她倍感温暖。“我到了俄语系以后,真有好像是回到家里的感觉,很亲切,很多老师我从小就认识,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还叫他们‘叔叔’‘阿姨’,所以一开始跟他们在一起上课的时候,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李英男回忆道。特别令她感动的是,系里的老师们虽然俄语水平都很高,而且教学经验很丰富,但他们仍然不耻下问,经常来找她问俄语问题,非常爱钻研。李英男心里既高兴,又佩服,暗暗地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榜样,向他们学习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
上世纪70年代在俄语系工作的这段时期是李英男不断学习和成长的阶段,她向很多前辈虚心学习,积累了课堂教学和教材编写方面的宝贵经验,当时俄语系许多老师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至今令她记忆犹新。比如汪嘉斐老师和赵作英老师。那个时代有声教学资料非常稀缺,老师们只能自己录制,李英男经常和汪老师、赵老师一起到录音室去进行教学录音。汪老师喜欢唱歌,熟悉声乐,会用嗓子,所以就成了英男模仿的对象,她在工作时向汪老师学习了不少;赵作英老师也擅长唱歌,是男低音,很会运气,他也常在录音时教李英男怎么用嗓子和发声。为了提高自己,李英男在课余时间经常听苏联广播电台,模仿苏联播音员,慢慢地在发声方面有了很大进步。除了这种教学录音外,为了让课堂更生动活泼,老师们还想了一些别的办法。当时的条件下根本看不到俄文电影,于是李英男和同事们就自己找电影配音。他们选择了一部很受欢迎的儿童片《闪闪的红星》,分工给这部片子配上俄文台词。李英男不但负责翻译剧本,而且负责给小主角潘冬子配音,就这样大家一起为学生们创作出了俄文版的《闪闪的红星》。李英男对语言的敏感性和她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也很快得到了俄语系老师们的认可,蔡毅老师主编的《汉俄成语小词典》和肖敏等老师编写的《俄语常用词词典》都邀请她参与。如今回忆起这段时期,李英男还感慨万千:“很多年纪比我大的老师都来问我,他们搜集了很多俄语经典作品中的例句,不停地琢磨,也逼着我琢磨,我也去翻词典,结合自己的一些实践不断地思考。这确实加深了我对俄语的理解,也让我学会了怎么找俄语中的难点,怎样给母语不是俄语的人解释词意。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让我非常高兴,我觉得能够发挥一些作用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
······

长按识别上方二维码阅读全文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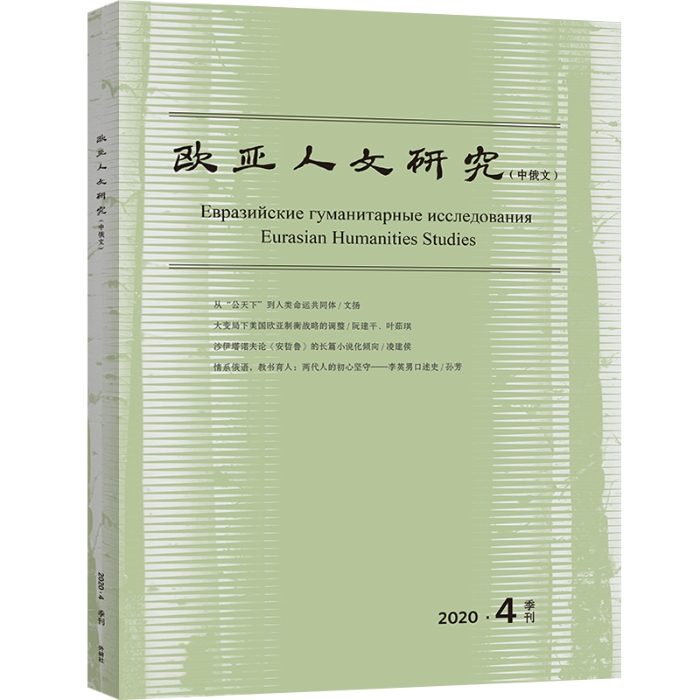
期刊简介:《欧亚人文研究》(原《俄语学习》)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协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面向国内外高校教师、硕博士群体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致力于打造外语类小语种科研成果的展示平台,发表与欧亚相关的原创性人文科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