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天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复旦大学 文扬
《欧亚人文研究(中俄文)》(2020年第4期)
提要:从中国传统天下政治的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全球化时代关于天下的终极表达,或者说就是终极天下;而围绕终极天下展开的政治,也就是人类历史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最后的天下政治。中国历史上的天下政治经历了“公天下”与“私天下”之间漫长的斗争,通过公与私、郡县制与封建制、政治与制度等多个方面的反反复复,近代之后逐步确立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共和国这一“公天下”国体。进入新时代后,“公天下”这一传统进一步促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政治倡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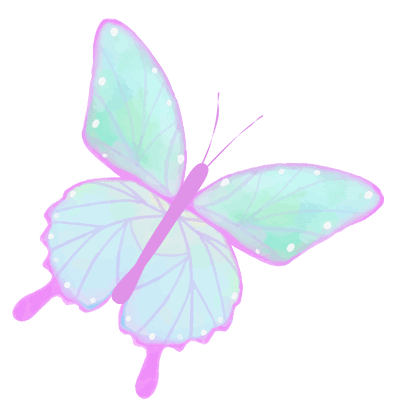
关键词:天下政治;公天下;私天下;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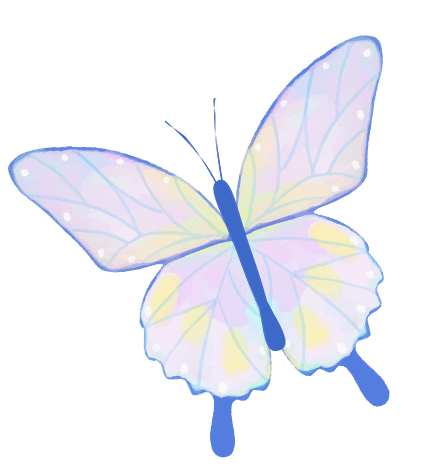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全新的政治观念是在2013年诞生的,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率先提出,随后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并被写进联合国重要文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今年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这一观念中的深刻内涵更加充分地反映了出来,并被全世界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了。正如近几个月里习近平反复强调的,“疫情在全球蔓延再次表明,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必须团结合作、共同应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由中国最高政治领袖面向全世界提出,中国人会觉得理所当然。这个观念提出后,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认同,而且通过今年这场始料不及的全球疫情彰显出其正确性和预见性,中国人也觉得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好理解之处。
这并不是说,仅仅因为中国是当今数一数二的世界大国,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号召力,所以才产生这种以全人类的立场看待全人类问题的全球政治倡议,此举的背后显然还存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因素。回看一百多年前,中国尚在历史的低谷中挣扎徘徊、以救亡图存为第一要务时,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是以“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最高理想,致力于“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康有为也在那个时期先后写过《人类公理》和《大同书》,自言“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唯行大同太平之道哉”。
考虑政治问题并不限于一国,也不一定是从本国出发,而是直接从全人类的问题开始,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一直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全人类”这个概念虽然是现代的,由世界190多个国家、全球70多亿人口、智人10万年演化历史等科学概念所规定,但其实在中华政治哲学传统中“天下”这个概念就包含了“全体人类”这个意思。而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政治理论与实践,也一直就是将“全天下”作为政治问题的起点。“天下无外”“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等信念,也是针对全人类政治问题的解决之道,与今天所说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从根本上讲是一以贯之的。
因此可以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观念不是别的,就是全球化时代关于天下的终极表达,或者说就是终极天下;而围绕终极天下展开的政治,也就是人类历史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最后的天下政治。
1.中华传统中的天下政治
天下政治,顾名思义,就是以天下作为问题中心的政治,与之相对的,就是列国政治,只以本国作为问题的中心。
以本国作为问题的中心,政治问题只限于本国疆域范围,完全不涉及天下。如果是城邦国家,例如古希腊,一群相距不远、各自独立、人口只有数千到数万规模的城邦国家,从一个城邦看出去,就是其他的城邦,局限在一个很小的世界里,根本不能形成天下的观念。虽然发展出丰富的政治学说,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分类的学说,但其实也只限于城邦国家的层次,与天下政治基本无关。即使是包括了众多城邦和周边疆土的领土国家,例如西欧的法国、英国、奥地利等领土国家,由于不是在一个广阔的疆域内逐步扩大而成,没有长期定居的历史,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理中心,也难以形成天下的观念。按照哈尔福德·麦金德(H.Mackinder)在1904年《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中的历史观:欧洲各国的起源不过是公元5世纪亚洲人大规模入侵的结果。他写道: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很有可能就是在那时被驱赶过海,在大不列颠岛上建立了英格兰。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帝国各省的居民被迫第一次并肩战斗在沙隆的战场上,从事抗击亚洲人的共同事业,并在不知不觉中结合成了近代的法国。(麦金德,2017:56)
另外,“为了抵抗这些入侵,在边境地区诞生了奥地利,要塞化的维也纳则是查理大帝的战役的结果。”“最终,新的游牧部落自蒙古来到这里,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位于北方森林里的俄罗斯公国成了蒙古金帐汗国的附庸。”(麦金德,2017:56)
以上国家的起源历史与中国大不相同。在西方学界,一直有一个所谓的“中国历史起源悖论”,学者们发现,中国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独特性在于,其历史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起源。正如基辛格在他的《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所说的,“早在黄帝之前,就已经有了中国。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而无须创建的既有国家。”(基辛格,2015:39)
的确如此。根据传说,黄帝之前早有巢燧羲农,继而是共工氏霸有九州,然后是蚩尤氏和有苗氏逐鹿中原,直到黄帝的子孙们入冀豫,迁三苗,再霸九州。好像这个神秘的“九州”一直就在那里。
而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工程也为传说提供了切实的证据。实际上,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所发现的新石器时期“六大区系”遗存,以及多元一体的文明发展进程,揭示出在中华文明早期阶段,的确有一个区域广大、近乎圆形的定居中心区和生产中心区,先于任何征服者和国家创建者而存在。(苏秉琦,2016:39)而这个大规模的、连续的定居文明区域,就是基辛格所说的中国“只需复原,而无须创建”的那个自然地理基础,也就是那个先于早期国家而存在的“九州”。
显然,“天下”的观念,就是从“九州”这个特殊的地理格局中产生的,由“九州加四夷”共同构成的“天下”大于任何一个国家,而且先于任何一个国家。这是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没有出现的特殊情况。为什么中国人一直在称自己这块土地为天下?其他文明中却没有产生过这个概念?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据史书的记载,早在夏朝,其共主即被呼为天子,而诸侯则以“国”作为封号。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中商”“四方”“四土”等词已频繁出现,表示商朝人认为自己位于被东土、西土、南土和北土所环绕的中土。
西周早期,“天下”一词即开始大量见于器物典籍中,与之相关的“四方”“万邦”等用语被反复使用,将洛阳平原作为天下之中的“中国”概念也开始出现。“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理论便逐渐成形了。
由此可见,“中心—四方”格局的独特自然地理环境和“多元一体”的独特文明起源过程,为“天下”这一观念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而这一观念一旦形成就固定了下来,再也没有从中国的史书中消失过,自始至终成为中华文明独特政治哲学的核心观念。由于天下先于国家,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在建立之初就只是天下之内的列国之一,而不能是天下本身;由于天下大于国家,列国就不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更不具有至高无上性,而成了并列在天下体系之内的政治单元之一。于是,整个天下被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存在,在国家政治之外,不仅有国际政治,还有天下政治,政治首先从天下问题开始。
这是一个从天下到列国再到每个家逐级排列下来的政治体系,正如先秦的管子所言:“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仲《管子·牧民》)或如老子所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老子《道德经》第54章)
概言之,“天下”这一观念,从客观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文明起源过程中产生,又反过来被主观的中华政治哲学思想所固化,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中“天下政治”的核心观念。
2.天下政治的中止与再生
晚清以降,中华天下政治遭遇西方列国政治的强烈冲击,基于华夷之别和册封朝贡制度的天下秩序随之崩溃。民国后,天下的观念被废弃不用,列国成为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主导观念。
今天的世界仍然是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列国世界,没有哪个现代国家还可以成为中央之国和天朝上国。《联合国宪章》规定,各会员国主权平等。
在这样一个列国世界,“天下之中”“天下之内”的概念都没有了,“四夷”的概念也没有了,天下成了全世界,而全世界成了全球,作为列国之一的中国就自然而然抛弃了地理上的“天下之中”这一观念,只保留了“以天下为一家”的理想信念。
换言之,在当代世界,原本那个孕育出天下观念的“中心—四方”自然地理格局没有了,圆圆的地球上不会再产生一个可以被公认为是“天下之中”的地理中心,也不会再有围绕某一个地理中心而发生的“多元一体”的文明发展进程;表面上看,“天下”这一观念应该随之退出历史舞台了。
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如前所述,“天下”这一观念是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共同作用的产物。其诞生的客观基础是一方面,在人们主观意识中的政治哲学含义则是另一方面。尽管不再有“天下之中”这个地理中心,但天下大于国家、天下先于国家这两个天下政治的基本原则却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对于曾经具有天下国家身份的中国来说,虽然本国从天下国家的地位上退到了列国之一的地位上,而且也已通过自身的现代化转型成功地适应了作为列国之一的现代国家身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天下政治本身也随之消亡了。从中国的立场上看,天下大于国家、天下先于国家这两大传统天下政治原则在今天就是全球政治应当遵循的两大原则:全人类大于各主权国家、全人类先于各主权国家。
而之所以中国的立场可以成为全世界的立场,全球政治的原则也由中国给出,是因为作为曾经的天下国家,中国不仅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内含了天下结构,而且在很长时期里几乎等于天下,既有完整的理论,又有丰富的实践,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的。
历史上全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也曾内含了天下结构,但公元5世纪覆灭之后再没有完整复活过,此后的西洋世界一直是列国混战的世界。7世纪之后的阿拉伯帝国和13世纪的蒙古帝国,在其全盛时期也都曾内含了天下结构,但两者都寿命太短,还没来得及理解何为天下,也没来得及学会治理天下,就在内部争斗中分裂成了列国世界。近代以后的西方是历史上第一次以全球为天下,虽然有过短暂的单极时刻,但并未比阿拉伯人和蒙古人强多少,同样是不懂得何为天下,终于还是退回到了列国林立的世界,直到今天。
3.“公天下”溯源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其他的大小帝国都没能将天下国家的地位维持长久?为什么历史上只有中国是真正的天下国家?为什么在当今世界“天下”这一观念仍具有现实意义?
这就是“公天下”理想的伟大生命力。从观念自身的演化上看,天下的第一个境界是“天下无外”,第二个境界是“天下为公”。从第一个境界到第二个境界的升华,就是孔子的伟大贡献。历史证明,只有做到了“公天下”的天下国家,才能“可久可大”;不能做到“公天下”的天下国家,就不可能长久,也不可能长大。《六韬·文师第一》载周文王与姜太公对答。文王曰:“立敛若何,而天下归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也就是说,天下本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客观存在,没有人可以擅取它,只可以与天下人同有;天子的位子随天命而改变,天下本身却是永世的,属于所有天下人。这就是“公天下”的含义。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公天下”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可以说,一部中华天下国家史,就是一部“公天下”与“私天下”的斗争史,就是一部“公天下”从理想到现实的实践史。
这部特殊的历史,需要从运动的源头处说起。杜佑在《通典》中写道:“三代以前,天下列国更相征伐,未尝暂宁。陪臣制诸侯,诸侯凌天子;人毙锋镝,月耗岁歼。自秦氏罢侯置守,两汉及有隋、大唐,户口皆多于周室之前矣。夫天生烝民,而树君司牧,语治道者,固当以既庶而安为本也。”
通过这段话,可以澄清今人关于“公天下”的一个观念误区,即认为“公天下”主要是指对于皇帝一人专制的反动;这个误区显然是西方中心论思想观念误导的结果。回溯中华历史,在古人的观念中,“公天下”首先并不是与皇帝那个统一“私天下”相对,而是与众多诸侯国四分五裂的列国“私天下”相对。诸侯封土建国,每一块领地之内就是一个国;而由割据分裂、追逐霸权的列国合并起来的天下,从天下本身来看,是一个最坏的“私天下”;因为列国“私天下”注定“更相征伐,未尝暂宁”,人民必然“人毙锋镝,月耗岁歼”,也就是春秋公羊“三世说”所说的“据乱世”(《公羊传》)。
“据乱世”的转机是“霸政”时代来临,因为“霸政”时代就是天下一统的最后阶段,诸侯国在争霸天下的同时,客观上加速了列国兼并、天下一统的历史进程;如齐桓公、晋文公之霸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韩非子·十过》);最后经历战国七雄混战,直到秦朝统一了天下;紧接着秦朝又“罢侯置守”(王夫之《读通鉴论》),通过郡县制彻底消除了“私天下”的列国基础。从此以后,天生烝民,“以既庶而安为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这可以理解为是“公天下”战胜“私天下”的第一阶段,即“公天下”与国家统一的一致;没有统一也就谈不上“公天下”,只有混乱不堪的“私天下”。与国家统一相联系的皇帝制度,虽然在个人动机上仍是为私,但在实现和维持统一这一功能上,却成就了公、抑制了私。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得很清楚:“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王夫之则有更深一层的判断,他在《读通鉴论》中写道:“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
当然,统一之后并不意味着“公天下”的自动实现;而且即使统一后的国家实行了郡县制,具有“公天下”的制度基础,没有恢复封建制,却也还没有一劳永逸解决问题,还要看统治者如何施政,如何治理。这可以理解为是“公天下”战胜“私天下”的第二阶段,即“政”与“制”的协调一致。正如柳宗元在《封建论》中针对“周事”和“秦事”所做的区别:“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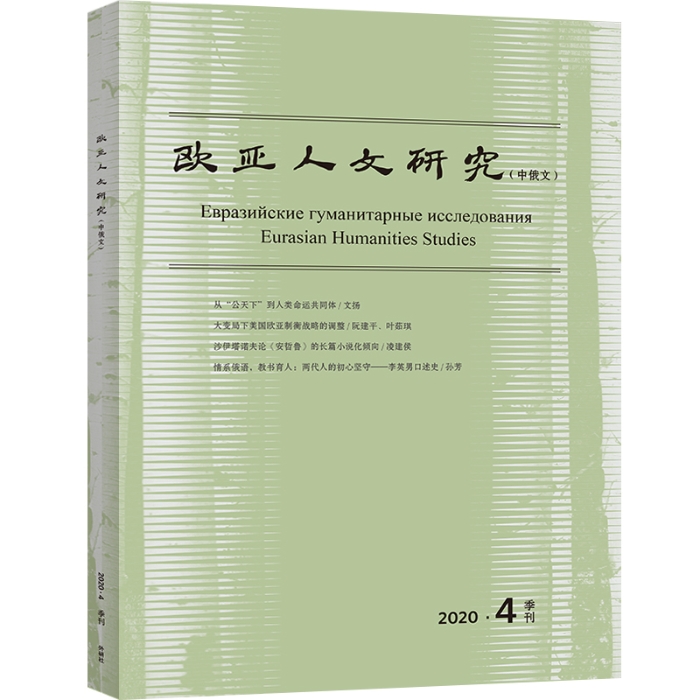
期刊简介:《欧亚人文研究》(原《俄语学习》)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协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面向国内外高校教师、硕博士群体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致力于打造外语类小语种科研成果的展示平台,发表与欧亚相关的原创性人文科学研究。



